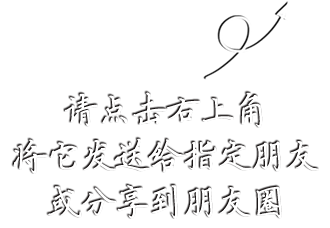桃园俯瞰图

桃园入口
钧 希在桃园路和桃园三巷相交的西南角,有一处很小的城市公园——桃园,南北向的桃园路和穿插其间东西向的桃园诸巷都是因桃园的故事而得名的。
上世纪3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太原城西之外的一片荒滩,因西临汾河而常被肆虐的洪水侵袭。1930年,阳曲县一位党姓财主购得这片土地。财主颇具雅兴,购得这块土地后并没有组织开荒种粮,而是雇了些精通园艺的花匠,种植了些既有观赏性又有经济价值的桃树和杏树,并在四周筑起了围墙,让这片西郊荒滩变成了一座园林。每逢桃红杏白之际,这儿便成了当时太原人踏春、赏花的好去处。后因战乱等诸多因素,这里的桃树和杏树未能保留下来,只有桃园这个名字沿袭至今。
桃园对我来说太熟悉了。熟悉到它的每个季节,每处景致,我都从每个角度观察过;熟悉到它的每方土地,每棵树下,甚至那座从我记事起到现在都依然存在的、漆面早已斑驳的儿童攀爬架,都有过我的足迹。
除去外出求学的几年,从我出生、上学、回到太原工作再到我儿子的出生、上学,我的生活轨迹一直都在桃园附近。就像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在我近40年的生命里,桃园与我的缘分从未间断。
桃园很小,小到依我看来“小”即是它最大的特点。小到站在门口的两级台阶上就可以将整个园子一览无余,小到只需几分钟便可把整个园子逛遍。公园大门是红色的,几十年来未曾变过样子,时间久了,翻修也仅仅是简单地粉刷而已。拱形的门洞上写着“桃园”二字。往里走几步有一座假山,与其说是假山,不如说是一小堆石块和水泥的混合物,几棵树和一些灌木就足以将它的真容掩藏起来,颇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假山再往后些,有一条长廊和一座亭子,长廊不长,廊顶是由藤蔓和树冠构成的。亭子是六角攒尖顶,朱身绿顶,坐落于灰白色石质的基底上。若是夏季夜晚,会有附近居民在此纳凉,三三两两的谈天说地声盖过了蝉鸣鸟叫,很是一番热闹的景象。
儿时,大人们称这座园子为小桃园,而孩子们更愿意呼作小花园,或是小公园。这园子里不仅有桃树,还有杏树、柏树、柳树和蔷薇,每逢回春之际,柳条上隐隐绿珠,桃枝上点点红斑,杏枝上也挂些许白色,这些稚嫩却饱含生命力的色彩被北方冬春之际独有的天色所笼罩,像极了莫奈的花园。
那时园子门口会有固定的几名小贩儿,摆摊卖些小玩具,路对面有所桃园小学。每逢放学时分,总有不少孩子围在摊前,若正巧接他们的是老辈,大概会买上两件,孩子们得到了喜欢的物件,摊贩挣到了糊口的钱,老人们也因孩子欢喜而面露微笑。
园子北边,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一排露天的台球案,台面因常年的日晒雨淋而破旧坑洼,因此大人们鲜有光顾,在这里打台球的,更多的是附近的学生,花五角钱可以打一局。台球这种发源于欧洲的绅士运动,在还没有球杆高的孩子手里,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后来,这里的台球案撤了,取而代之的是露天棋社,一众民间高手在此对弈,“观棋不语真君子”在这里显然不适用,双方棋手尚在构思棋局,观战的人已忍不住要上去拨弄一番,更有甚者会因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若是棋手没按自己的方法,还会喋喋不休地劝说。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去得太多、太频繁的缘故,成年后的我就很少去桃园了。哪怕是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必会经过,桃园也只是路边随处可见的一处地标而已,和必须要经过楼房、路口一般,并无二致。随着城市的建设,更新、更大、乃至功能更完备的公园不断建成,有玉带般贯穿城市的汾河景区,有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域公园晋阳湖公园,还有经改造后焕然一新的迎泽公园、龙潭公园、文瀛公园……这些公园,或历史厚重,或体量庞大,或精致奇巧,桃园和它们比起来就显得有些式微了。
今年春季的花期,与桃园一路之隔的杏林七条成为了一处网红打卡地。短视频和流量的兴起,使一些原本平常的事物有了新的含义。那些日子里,在我上班途中路过时,总会见着许多身着汉服或骑着机车的年轻人在杏林七条的路牌和海棠花下打卡拍照,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转眼已是岁末,见过春的热闹、夏的喧嚣、秋的多姿的桃园,在初冬就显得有些寂寥了。我望向不远处的桃园,它依旧在那里,仿佛一直在静静地端详着发生在墙外的热闹或冷清。此时,我终于明白,并非是我因年岁的渐长而变得喜新厌旧,而是桃园已经成为我生命里的一处烙印,它不再是一处地理坐标,不仅是一座再熟悉不过的公园,而是我心中家的概念,是我对生于斯、长于斯,也许将来也会老于斯的家乡——太原永久的情愫。
李 红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