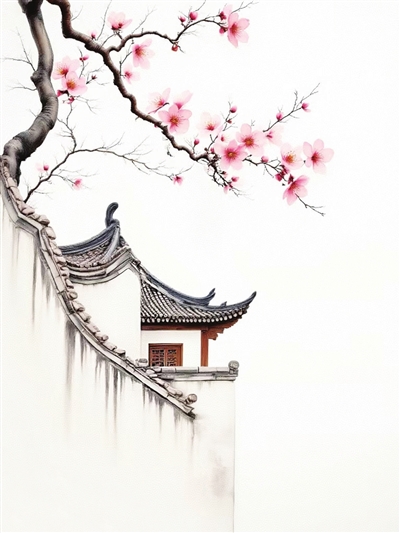郑惠俊
当春风的指尖掠过汾河水面,太原的泥土便悄然苏醒。这座被群山环抱的古城,总以特有的从容迎接季节更迭。不同于江南的烟雨迷蒙,亦非岭南的喧闹花海,太原的春色像一位提笔蘸墨的画家,将黄土高原的宣纸徐徐铺展,先是一抹淡白,继而洇开粉红,最终晕染成漫山遍野的锦绣。杏花与桃花,恰似两位琴瑟和鸣的伶人,在春的序曲里,以不同的韵律叩击着人们的心弦。
最初打破寒冬沉寂的,是那些虬枝盘曲的老杏树。它们仿佛从《齐民要术》的泛黄书页里走来,在万柏林生态园的沟壑间织就万亩雪色。晨雾未散时登上观景台,会看见整片山谷浮动着云絮般的花影,待朝阳将金粉洒向枝头,才惊觉那是千万朵含露的杏花。老杏树总带着岁月的风骨:皴裂的枝干如青铜器上的纹路,托举的花簇却似少女捧出的新雪。新栽的幼树则更显灵秀,斜倚在汾河堤岸的几株,总爱把花枝垂向粼粼碧波,让倒影与游鱼追逐嬉戏。最动人的是雨后初霁时,被雨水浸润的花瓣泛着玉质的光泽,风过时簌簌抖落的水珠里,映着双塔寺的飞檐与晋祠的铜铃,恍若将千年古城的倒影装进水晶球中。
总有人驻足在杏花树下细嗅芬芳。穿羊绒大衣的老者会想起童年时,母亲用杏花煮水给他祛咳疾的旧事;戴红领巾的孩童踮脚数着花瓣,争论着绛红与素白花萼哪种更美;扛着三脚架的摄影师屏息凝神,等待一只蓝尾鸲掠过花枝的刹那。而在街角的面馆里,老板娘将新摘的杏花浸入醋坛,说是要酿一瓮“杏花酸”,待到暑气蒸腾时给客人解腻消暑。这些细碎的烟火气,让原本清冷的杏花平添几分温润,就像老陈醋的酸香里总藏着粮食的醇厚。
当杏花的雪浪渐次退潮,桃花便以燎原之势点燃了整座城池。晋阳湖的桃花岛是这场盛事的中心舞台,六千株桃树将湖岸染成粉色的梦境。若说杏花是工笔白描,这里的桃花便是泼墨写意:临水的枝条斜斜探向湖心,倒影与游船相映成趣;坡地上的花丛则如打翻的胭脂盒,深浅不一的红从山顶流淌到脚边。常有穿汉服的少女执团扇穿行其间,绯色裙裾掠过青石板,惊起几片落英,恍惚间竟让人分不清今夕何夕。而在太原植物园的桃花园里,绛桃、碧桃、山桃等三十余个品种次第登场,从浅粉到深红的花潮绵延数里,仿佛把《诗经》里“桃之夭夭”的意象铺展成流动的画卷。
桃花的生命力总带着几分野性。那些扎根在蒙山峭壁上的野山桃,无需园丁修剪施肥,依然能在料峭春寒中开得恣意。深褐色的枝干嶙峋如铁,托举的繁花却娇嫩得能掐出水来,这般刚柔并济的美学,恰似太原人骨子里的性情——既有黄土高原的粗犷,又存晋商故里的风雅。老人们常说,从前物资匮乏时,孩子们会把桃花瓣夹在窝头里蒸熟,让寡淡的玉米面也染上春日的香甜。如今虽不再需要以花充饥,但主妇们仍会在晨练时采几枝带露的桃花,插在粗陶罐里,让陋室也生辉。
赏花人的情态亦是风景。犹记去年在桃花沟的蜿蜒小径上,一对银发夫妇携手漫步,老先生用手机拍下老伴与花同框的笑靥;背着画板的少年坐在古杏树下涂抹油彩,却总嫌调色盘里的粉红不够灵动;穿冲锋衣的登山客在榆叶梅花海中支起帐篷,任花瓣飘落成清晨唤醒他们的闹钟。最热闹的当属周末的晋阳湖畔:风筝在花海上空舞动,孩童的嬉笑惊飞觅食的麻雀,卖糖葫芦的小贩推车穿过花荫,玻璃柜里的山楂裹着晶亮的糖衣,与桃花争艳似的泛着红光。这些鲜活的场景,让静态的花海有了呼吸的韵律,仿佛整个太原城都随着花开花落的心跳而起伏。
有时一场夜雨不期而至。晨起推窗,薄雾中的桃林宛如罩着轻纱的美人,湿润的空气中浮动着蜜糖般的芬芳。细看会发现,雨滴将花瓣洗得透亮,那些原本就明媚的粉色,此刻更像浸过晨露的锦缎,泛着丝绸的光泽。这样的清晨,连环卫工人都放慢了清扫落花的动作,任粉白相间的花瓣铺成天然地毯,让赶早班的行人踏着花香开始新的一天。待到正午云开雾散,阳光穿透花枝,在地上织出斑驳的光影,常有老者在树荫下摆开象棋盘,棋子叩击棋盘的声响,与蜜蜂采蜜的嗡鸣合成春日特有的和弦。
当桃花的浪潮渐趋平静,丁香便以暗香浮动的姿态悄然登场。虽不及杏桃的绚烂夺目,但那成串的紫色花穗总让人想起戴望舒笔下的雨巷。文瀛湖畔的丁香丛中,捧书的学生在香雾里徘徊,不知是在温习功课,还是在酝酿写给某人的诗行。而散落在街巷角落的连翘与海棠,早已将明黄与绯红悄悄缀满枝头,如同春日的余韵在轻轻叩打窗棂。
这座古城的花事从来不会戛然而止。当暮春的柳絮掠过双塔寺的琉璃瓦,太原人早已将这份绚烂藏进记忆的锦囊——毕竟再匆忙的岁月,也该为绽放留一方天地。而那些渗入灰砖黛瓦的花香,正静静等待下一个轮回,在来年的风起时,再次破茧成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