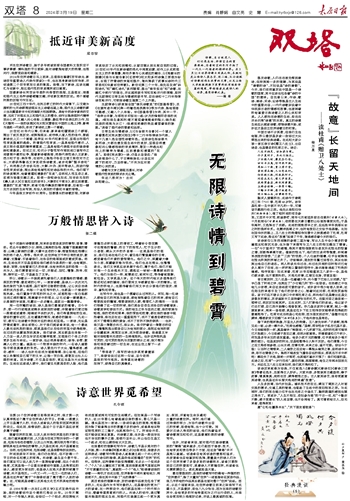关注世界诗歌日,始于多年前读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的节日致辞,她对诗歌抱有极大的热情,也很内行,我颇受启迪和激励。
2024年世界诗歌日马上到来,正值我在编著《百年诗光:新诗百年重要诗人代表作荐读》一书,也在思考新诗如何传承、并创造第二个百年更加壮美的景观。我想,当下新诗,应该在融汇与创新中,抵达现代性的审美境界或曰高度。
回溯新诗长河百余年曲折而浩荡的流程,正是现实、浪漫和现代主义各种诗潮碰撞交融,并创新发展的历史。两个高潮时段的历程可作见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救亡的时代大背景下,以艾青为旗帜的七月诗群推进现实主义诗潮迅猛上涨,现代主义诗歌的薪火也在戴望舒手中和西南联大校园燃烧。具有中西诗学素养的艾青,完成了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整合,创作出既表现时代精神民众心声,又融入内心体验,以意象、象征等手法表达的力作,如《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影响与造就一代诗风,形成了新诗史上第一个高潮。
20世纪80年代以降,归来者、新来者和朦胧诗三个群落,推出了或反思历史、或拥抱现实、或呼唤人道人性的佳作,掀起新诗史上又一个高潮,延伸至90年代和新世纪,呈现出向现代性审美提高的趋势。所谓现代性审美,一是具有现代意识、人类文明价值观的精神意蕴美,二是具有现代表现手法的语言修辞和意象美。世纪之交,知识分子智性写作同民间口语写作之间曾展开激烈论争,随着新诗潮涨落,两派代表性诗人王家新、西川和于坚、韩东等,在创作上既恪守各自立场又吸收对方之长,大都获得鲁迅文学奖优秀诗歌奖,逐步和解“握手言和”了。而两派之外吉狄马加、大解、叶舟、梁平等诗人,则进行综合性审美创造,推出具有地域性和史诗品格的大作。他们笔下的诗美境界,有着意蕴和意象的“双美”,自然和人性互动之美,宏阔与细微交融之美。即使一些短诗也如此,如吉狄马加的《彝人谈火》《古里拉达的岩羊》,大解的《干草车》,都达到意蕴、意象的“双美”境界,前者可视作彝族的精神画像,后者如一幅北方农民的生命写照,均给人深刻的印象和丰富的联想。
今年是我文学创作60周年。回顾漫长的诗歌历程,对新诗审美经历了从无知到略知、从盲目随从到比较自觉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在新诗潮的洗礼中再度启蒙,创作上从此前现实主义的外景描摹,转向外景与心灵感应的融合,以《检察长的眼睛》《我与长城合影》《红领带》和太阳系列诗集三部曲为标志,实现了抒情诗的突破和提升,继而捧获了叙事长诗时代三部曲和《华夏创世神歌》。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先后发表“斜阳诗札”和“融汇诗札”系列随笔,提出“衰年变法”和“诗歌,在融汇中前行”的理念,并实施两极书写和双轮并行的策略,即时代主旋律和日常生活与情感两极书写,自由诗和十二行半格律诗双轮并行,可称我诗歌生涯第二个上升期。
主旋律诗以获首届全国“绿风诗歌奖”的《国魂浩荡》,及《在黄河老牛湾》《乘一列曙色地铁跨年》等为代表,既有现场可触感,又融入个人体验。举《国魂浩荡》为例,其中一节:“我伸出手掌,与那枚手印贴在一起/岁月的烽烟叩动我的灵魂。/假如我生逢其时/敢不敢迎着侵略者的炮火/肩负起民族的危难与兴亡?/我感觉前辈的热血激荡着我的脉跳。”具备了现代诗的要素和品质。
日常生活与情感诗,以《与金银木合影》《一个盲人来看莲花》《雨夹雪》《陌生》等十二行半格律诗为代表,有十几首入选全国性诗歌年选。这些诗包括金银木系列诗,大都注意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呈现自然意象和内心情感相映的审美境界,散发一种趋光和向上的精神与情趣,达到意象和意蕴的“双美”。即使《雨夹雪》一诗,仍显从容姿态:“我也该做些什么了,于古稀转身处/从容应对脚下的泥泞,乃至疼痛。”不失为应对困境的心灵的美。
诗歌与文学之路阻且漫长,对诗歌现代性审美的探求永无止境。
年近八秩何为?去问斜阳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