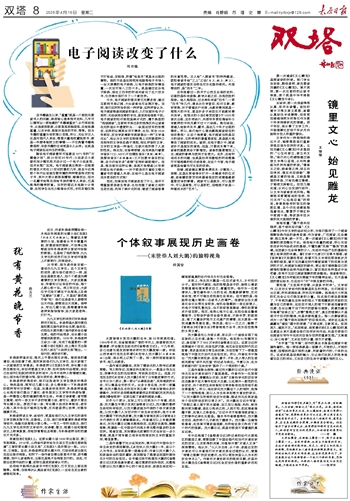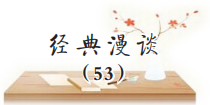王珊珊
第一次通读《文心雕龙》是刚读研的时候。同门学长告诉我,跟咱老师,首先要读刘勰的《文心雕龙》。果不其然,第一次见面列的必读书单里,首个就是中华书局版《文心雕龙今译》。
实话讲,那一次我读得很认真,却并未读懂。虽如初高中习得文言文那般,逐篇认真标注字词解释,但却更加疑惑导师为何将它作为数十年来持续研究的课题。若干年后,我从事了文学工作,开始理解它历经千年岁月而始终为世人所重的缘由。
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多提到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我们内心的感悟通过语言文字得以呈现,从而构建起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感是文章的经线,文辞是情理的纬线,只有先确立情感,才能使文辞畅达。后世几循此道,从内心出发进行创作,以文字与读者形成共鸣。陶渊明采菊篱落间的悠然,早已化作“心远地自偏”的哲思;李清照卷帘时惊见的绿肥红瘦,至今仍在词章里摇曳着泪光;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将家族半世兴衰织成大观园的梦影。
细细思量,“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中对文学的品评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阅读理解经典作品的参考答案:作为读者,广泛阅读、社会磨砺、独立思考,缺一不可。第一次通读《文心雕龙》而不能理解的原因概在于此。我没有大体量的阅读,所以无法形成评判作品优劣的基础,不懂刘勰“风骨”“隐秀”的真章;也因缺少社会背景的介入,无法对作品产生的基础和意义有深刻的体察。看《古诗十九首》只见草木摇落,读《卖炭翁》只觉墨色苍凉,却看不见文字背后那些被岁月压弯的脊梁,看不见刘勰在时代褶皱里埋下的叹息与凌厉的不甘;而阅读与阅历的缺失,更让我不能根据自己的感悟和理解去品味作品的魅力,盲目地在各种观点中迷茫着,却寻不见自己阅读理解的那条蹊径。我逐渐明白,《文心雕龙》为何能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坐标。它不是凝固的理论标本,它应在今“识”中焕发新的共鸣。
要知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创作,以及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是双生的河流。它们同迎日出日落,时而波涛汹涌,时而风平浪静。流淌间大小河流的汇注会让它们焕发新的力量。如此我们便容易理解了,千年前刘勰在定林寺的烛火下挥笔蘸就的齐梁的风露与自己的春秋,在后世不同人的笔下不断添加着新的注脚,生长出属于当下时代的筋骨与眉眼。就像刘勰当年既尊“经诰之正”,亦赞“楚艳之奇”,真正的理解从不是困守于旧识的缠绕,而是决断地重生。每一次解读都应成为一次“操千曲而后晓声”的自我完成。或许这正是刘勰藏在“通变”篇中的深意:“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此刻再读,我更意识到《文心雕龙》的真正教益从来不是教会我们如何评判作品,而是引领我们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对自我与世界的重新发现。“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文末这句的分量,我方才读懂。
“本乎道”“变乎骚”,创作的真实本身是在阅读中被建构着的。每一部经典都是一面镜子,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回想到的是不同的光影,折射着时代的、个体的光芒。这或许就是经典的魅力,它让我们在别人的思考里看见自己的成长,又在自己的生命中读懂永恒的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