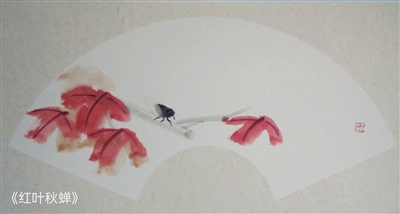我很爱吃咸鱼,因为我从小最早接触到的就是咸鱼,山西的北部那时候人们还不怎么吃鱼,要吃就是从南边运过去的那种咸带鱼,咸带鱼可真咸,但它必须咸,要是不咸也许在路上就臭掉了。咸带鱼我以为特别能下饭,用油煎煎,煎到两面黄,一块儿我就可以下一碗饭,后来几乎是养成了习惯,鲜鱼倒好像不如咸鱼好吃了,山西北部那时候好像不怎么出鱼,但也不会缺鱼,像什么鲤鱼、鲢鱼、草鱼、鲫鱼,还有那种叫“白条”的小鱼——这种鱼好像永远长不大,就一拃来长,但银光闪闪的可真是好看,家父喜欢买大量的白条回来腌,腌好了再晒,喝酒的时候会从竹笥里摸出几条在火上烤烤,以之下酒不赖,这种鱼收拾起来特别的麻烦,因为其太小,一条一条接着又一条地开肠破肚让人看着好不心烦,我看着父亲在那里收拾鱼,日影在慢慢移动,一上午不知不觉过去了,日影慢慢慢慢移动,一下午又不知不觉过去了,父亲可真是有耐性。那时候家里有个铁箅子,上边总像是有股子咸鱼味,父亲喝酒,经常就这种小鱼干。这种俗名叫“白条”的鱼我无师自通地认为它就是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所说的“鲦”,王维的这篇文章写得真像诗一样,也许可以说诗也不及它: “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
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因驮黄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维白。”
咸带鱼现在好像还能买到,做咸带鱼不必惊动葱姜酒醋各种的调料,简直是什么都不要,洗好切段上笼蒸然后再放到油锅里煎,真是很好吃,简单而好。我现在吃饭,如果是别的菜,我也许会吃两小碗,而如果今天有油煎的两面黄咸带鱼,那么我也许就会吃三碗到四碗,真是“无事大饱,罪过罪过。”
但我还是希望有咸带鱼吃,极咸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