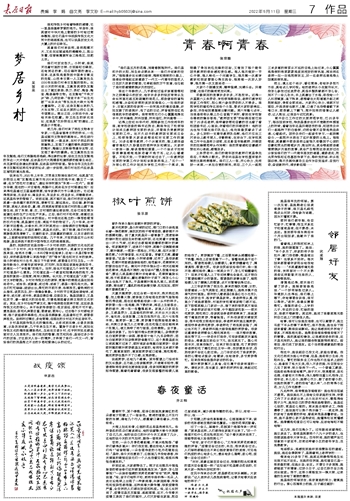夏天吃煎饼,是小时候的记忆,街门口的小块地里长着一棵花椒树,黑沉沉的枝干弯弯曲曲,像舒展不开的胳膊和腿。到了夏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茂密细碎的绿叶把它送回生命的高光时刻,还在周遭十步氤氲出一片小气候,过来过去都能闻到馥郁的椒叶的麻香。邻家摊煎饼了,进来打个招呼,就端个空碗随便摘了,椒叶稠密,一茬顶一茬地出,不怕人摘,但不兴毁了嫩花椒。“小时绿蛋蛋,长大红蛋蛋。穿着叉叉裤,露着黑蛋蛋。”这是个谜语,小时候老猜,记牢了,是母亲教的。花椒叶两面都是绿油油的,油性黏手,花椒树味大的缘由也在于此。摘完叶子的手指头过一两天还能闻到花椒味,洗是洗不掉的,有句话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挪这儿就是摘过椒叶手有麻香。花椒树遍身长刺,枝干杈茎都长,藏在密集的叶子底下,再怎么小心指头也免不了挨扎,于是摘椒叶难免扎刺儿,到花椒成熟,刺也硬了,蓬乱的枝杈纵横交错、拉拉扯扯,那时最不爱摘花椒了。
大夏天摊煎饼,在灶台前一站半天,热天热灶热鏊,加上烟熏火燎,厨房里又没有现在的排气扇抽油烟机等设施,现在还能想起母亲一抹一头汗的样子。煎饼要一张一张地摊,挑下熟的来,再舀上生面浆去,熟的晾开,再一张一张叠摞起来。家里人口多后生多,又都是劳力,正是能吃的时候,天天出大力流大汗,食无肉,全凭饭撑,三张四张挡不住,五六七张很平常。摊煎饼一累二费,煎饼属于粗粮细做改善生活,而爽口多食乃人之常情,往往吃饱之后还能再来个双摞儿,便又捎带了两勺面浆,自然费粮。至于累,就是母亲累了。如今城市街头的煎饼摊儿,杂粮煎饼比白面煎饼贵一块钱,顾客却十有八九买杂粮的,因为白面煎饼不如杂粮煎饼香脆可口,这个账要是放在以前就算不过来了,那时谁家舍得摊白面煎饼?母亲那时摊的椒叶煎饼都是玉米面的,有两年玉米都不够吃了,摊高粱面的,高粱面煎饼涩口涩嗓,难吃难咽,摊成煎饼也提升不了口感,实难恭维。
说起煎饼,还有几个趣事。某年媒婆上门给成年的兄长提亲,正巧赶上母亲摊煎饼,不便离手招呼,媒婆便陪同母亲站在厨房里说道,母亲用刚摊好的煎饼招待媒婆,摊着吃着聊着,母亲发现搽鏊的油碟儿里的油没了。煎饼摊好下鏊,之后要用麻头刷蘸油搽一下热鏊,再往上舀面浆摊下一个。搽鏊油就是干这个用的。媒婆把油碟儿当醋碟儿,拿煎饼蘸着吃了,搞清真相,媒婆大笑。母亲当笑话说给我们听,我一直不信:醋和油呀,鼻头一闻就分开了,怎么可能蘸着吃了?后来才知道人上了年纪味蕾也会退化,这才明白了媒婆油醋不分的缘故。媒婆提的亲事也黄了,能把油碟儿当了醋碗儿的媒婆,点不对鸳鸯说得过去。
上三年级时换了班主任,新来的插队知青,女的,说普通话,一生气就脸红,就红眼圈儿,她根本镇不住淘气的村里娃。那时的儿歌都是《我是公社小社员》,没人好好念书,逃学旷课是家常。李老师很认真,班里少了谁她都要找,村里的学校离谁家街门都不远,放下粉笔就能上门家访一次,接下来的惩罚就不细说了。李老师家访我不知情,中午跑回家吃饭——那天吃煎饼,刚吃两口,母亲就说李老师前晌来了,我赶紧咽下嘴里的煎饼,等着挨骂。不料母亲那天满面笑容,很平和很文明地对我说,李老师来时她正摊煎饼,便招呼李老师吃煎饼,李老师吃了两张就说饱了,再让也不吃了,李老师叫她大娘夸她摊的煎饼香。母亲还邀请李老师哪会儿想吃再来吃……我不想听故事,我在等下文——快动手打我呀,可母亲那副欢天喜地的劲头,倒像是见到仙女下凡,说完就完了。提心吊胆半天,结果没挨打。后来才明白道理,吃了煎饼的李老师和吃了糖瓜的灶王爷一样,没好意思告状,否则母亲不会这么放过我。上门告状还吃了我家煎饼,我的心情有点复杂,有腹诽,也有侥幸,多亏煎饼帮忙。后来没再给她提供家访的机会。
椒叶煎饼算不上美食,但它属于母亲味道的一种。清贫岁月,悠长夏日,窗外的声声叫卖,唤起记忆里的椒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