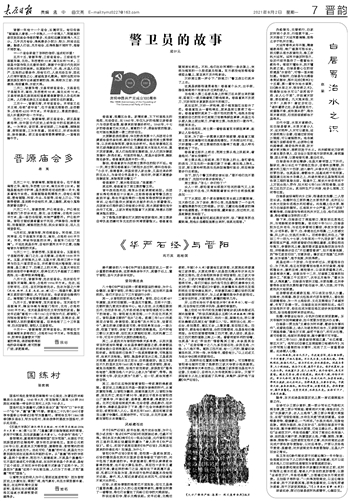大运河春秋末年开掘,隋唐通航洛阳,转广通渠可抵长安。到元朝从淮水改凿向北,竣工京杭大运河。运河开凿历时悠久,给历代官员提供了一整套治水教科书。做官不懂治水,则不懂执政之道。白居易最心仪的官职竟是“水官伯”,可惜一直未能如愿。年轻时,白居易与元稹备考策试制举,挥汗完成《策林》七十五篇,第一篇专为治水谋策,曰《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明确指出治水可以“保邦邑于危,安人心于困”,并说减灾防患,责在郡使。凡大难来临,天灾乎?人祸乎?唐玄宗叹曰,“诸州遭涝之处,多是政理无方,或堤堰不修,或沟渠未泄”,将水旱灾害成因,归结到官政郡治才是根本。
古代中国,水旱灾害频仍。在白居易看来,水旱灾害分人灾、运灾两种,人灾可以避免,运灾虽然难以全避,但通过官民有力措施,可以减轻损失。他告诫高层乃至郡县官员,必须持公道而施善政,调动各种手段,防灾减灾救灾赈灾,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州郡刺史乃防救灾害主要负责人,自当全力组织地方防涝抗旱,修筑堤堰,固土祈福,以期有备无患,逢凶化吉。
白居易治水言论精辟,也是大唐帝国上下共识。据研究,单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统计,自春秋至隋朝,共建水利工程六十四项,进入唐代,兴修水利工程达到一百零四项。也就是说,唐朝治水,远超此前千年积累。强国建立在治水功德之上,而诸州刺史正是指挥完成各项工程的直接主官。每逢开工,刺史大举动员成千上万民众投入劳作,如大和七年(833)河阳修堰,出动役工达四万之众。就当时生产力而言,有多么艰难,又何等壮观。
白居易途经南阳内乡之际,相逢老友张籍,二人彻夜长谈。张籍时任工部所属之水部员外郎,此时正以水务大臣身份巡视水利和漕运。而张籍上任水部,制书乃白居易所撰写。江淮旱灾十分严重,万千“疲民”嗷嗷待哺,白居易恰恰前往杭州灾区上任,他们此刻相逢,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接下来,白居易过了洞庭湖口,随即到达故地江州,与同龄刺史李渤相聚。昔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与这位李渤同日黜官,李改为资议参军,分司东都。眼下,白、李竟在江州相聚,二人百感交集,共上庐山,交流尤为深入。目前李渤江州任上,“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今年旱死一千九百多顷”,年景歉收现实严重,而财政昏官仍在横征暴敛,还要征收往年拖欠,李渤拼死上奏,强烈要求皇室免除百姓当年负担,并明确表示自己“不忍鞭笞黎庶”,如不准奏免赋,则“特乞放臣归田”,甘愿弃官。穆宗这才批复“江州所奏,实为诚恳”,准予免赋,州民得救。
就是这样一个好官,今夜举杯过头,郑重相告白公,为了抗旱,他正在积极筹划治理本州甘棠湖,准备筑堰安水,建桥定闸,调控湖水,以保旱涝灌溉之利。居易闻言大震。史载当年十二月,甘棠湖工程果然如期开工,“筑堤三千五百尺”,次年正月竣毕,“蓄水为湖,人得其赢”。白居易与郢州王镒、水部张籍、江州李渤等务实官员次第相逢于赴任途中,深入交流,对于执政杭州大有深意。
这些朝官彼此激励互勉,可以迸发出惊人力量。如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包括宋代苏东坡等人,皆在贬后励精图治,为一方土地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书写了功德一页。白居易在忠州同样如此。他们历经挫折不幸,却往往成为落后地区进步突变的难得契机,给当地黎民带来幸运祥光。
张籍、李渤坐论治水,令杭州白刺史深受鼓舞。乐天年轻时为民呐喊请命,如今更要为百姓兴办实事。
白居易一贯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番赴任路上,诗人与诸友热议治水,又亲眼目睹了洞庭浩瀚,“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利可兴社稷,害可吞黎民,他面对洪涛骇浪,胸中豪情不可平复。
长庆二年(822),居易途经洞庭之夏,“长江倒灌,湖区大灾”。他写出《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充分抒写难以遏制的治水情怀,完成了又一首重要诗篇。此诗撼人心魄:
江从西南来,浩浩无旦夕。长波逐若泻,连山凿如劈。千年不壅溃,万姓无垫溺。不尔民为鱼,大哉禹之绩。导岷既艰远,距海无咫尺。胡为不讫功,余水斯委积。洞庭与青草,大小两相敌。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我今尚嗟叹,禹岂不爱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观遗迹。疑此苗人顽,恃险不终役。帝亦无奈何,留患与今昔。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垂来亲指画。疏河似剪纸,决壅同裂帛。渗作膏腴田,蹋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
据考,乐天此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首记载洞庭水患之作。
全诗可分三部分赏析,第一部分写长江气势和大禹功绩;第二部分写洞庭、青草两片大湖,侵蚀农田,乃至“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第三部分希望大禹复生,实现“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的美好愿望。全诗想象奇特,雄健豪迈,一气呵成。“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说明白居易对于疏导水流、掘开堵滞的治水原理,已有正确认识。最后两句“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采用了刺史公务用语入诗,说的是大唐户部,执掌国家土地、户籍、赋税、军需、俸禄、粮饷等一应财政收支相关之事,而州府刺史必须完成户部各项年度指标,以对应考核。户部以及各地节度使、观察使,对州级刺史年考首要指标,正是人户田亩之增长。
张卫东在《唐代刺史若干问题论稿》一书中指出:各地刺史对治下人口的升降变动,甚为敏感,无不以促成本地人口田亩的迅速增加为首要施政目标。
白居易熟知刺史要务并亲履忠州刺史之职,此时怀抱终止湖水泛滥、增添人户良田的美好理想,以期“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力图通过治水尽刺史职责。正如陈子昂所说:“一州得贤明刺史,以至公循良为政者,则千万家赖其福;若得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为政者,则千万家受其祸矣。”(《上军国利害事·牧宰》)
详读此诗,探讨白居易彼时执政情怀,心胸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