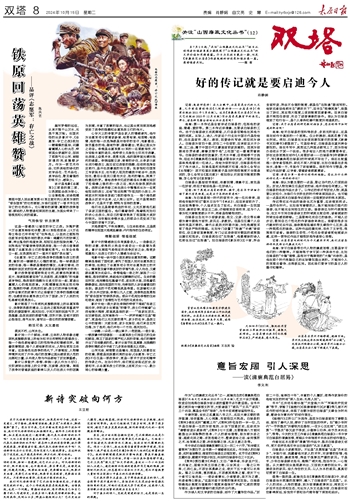王立世
关于汉语新诗突破的探讨,如果是针对个体,还有一定意义,对于整体,很难理清脉络,最多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罢了。因为百年来,艺术不断地受到各种干扰和冲击,我们对汉语新诗的认知摇摆不定。教科书上的有些诗歌,知名度远远超过一般诗歌,能代表汉语新诗的水平吗?大刊上有些堂而皇之的诗歌,一次又一次被质疑,能代表汉语新诗的水平吗?获各种大奖的有些诗歌,被炒得热度很高,却遭读者冷落,能代表汉语新诗的水平吗?汉语新诗处在什么阶段,恐怕没有几人能说得清。在这种状态下谈突破,也只能是局部的、碎片化的、理论性的。
我认为对百年汉语新诗必须清理门户,舍弃一些非诗的东西,捡回一些遗珠,还艺术以公正。对汉语新诗的评价,既不能迁就,也不能抹杀,要实事求是,成绩是成绩,问题是问题。既要纵向地看,更要横向地比;既要历史地看,更要艺术地审视;既要肯定其探索,更要指出其不足。只有辩证地看待,谈突破才能有的放矢。
我们对汉语新诗有了艺术标准和整体定位,才能找到突破的方向。这个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谁来做,也是一个问题。掌握话语权的,恨不得把自己和自己圈子的人写进诗史,在很多诗人看来是诗歌的耻辱。由民间来作,民间山头多,哪座山能做到公允?艺术史由后人撰写,越后越客观,但面对汉语新诗的众多瓶颈,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浪费了很多时间,错过了很多发展的机遇,制约新诗现代化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其实,谈方向比较含糊和空洞,艺术强调的永远是个体和个性,个体的突破才能带来艺术的春天。已经有一些开拓者使汉语新诗改天换地,绽放出时代耀眼的光芒。作为一名诗人,我也试图沿着前贤的脚步前进,写出隐喻人类严峻生态的《夹缝》和揭示人性的《这倒霉的梯子》。我的诗歌理想是批判不影响热爱、赞美不掩盖缺陷、追求现代不忘记传统,不惜一切为美和善鸣锣开道。艺术上厌恶“假大空”和文字游戏,喜欢以一个小而实的切入点进入,通过独特而饱满的意象抒写灵魂的隐痛,折射时代的风云,但总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不惜耗费大量时间去挖掘心中真正的汉语新诗歌。
艺术来不得半点虚伪,至于那些徒有虚名的诗人,用金钱等手段开道的诗人,其拙劣的文本是社会转型期光怪陆离的泡沫,对他们谈突破无异于说笑话,这类诗人及其诗歌必将在短暂的热闹后自生自灭!
对于真正的诗人,突破是前进的动力,也是困扰一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