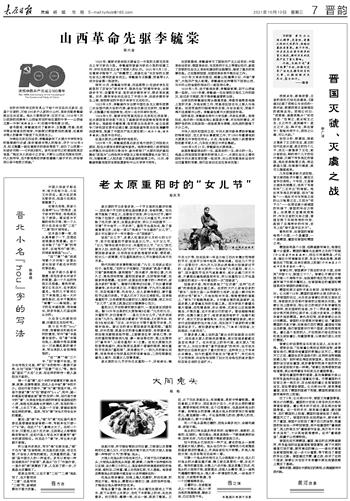西周末年,政局动荡,王室的危机已经无法避免,《国语》记载了郑桓公与史伯的一段对话,预测西周王室衰落后的政局走向。郑桓公问曰:“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史伯回答:“臣闻之,武实昭文之功,文之祚尽,武其嗣乎!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
史伯分析、预测说,周武王继承了文王的功业,武王的后代应该兴盛,武王的四个儿子,成王一脉继承了王位,被分封到应、韩的两个儿子的后代衰弱,只剩下河东地区的晋国,地处形势险要之地,周边都是小国,如果修行德政,就可以强盛起来。
几年后镐京被犬戎攻陷,晋文侯西赴关中勤王,辅佐王室东迁洛阳。十年后,又是晋文侯杀死周携王,结束了东周初年“二王并立”的局面。地处河东地区的晋国,因为“居险”——地处关中与河洛之间的山川险要之区;又因为“邻于小”——在周边弱小诸侯国的环绕下,晋国的号召力明显。在周朝王室遇到危难时,作为王室的兄弟之国,晋国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史书上说“晋于是乎定天子”。
春秋初年,在晋国的南面有两个小国,一个是虞国,一个是虢国,虞国在晋国和虢国之间。
虢国虽然是个小国,但跨越黄河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虢国的疆域北至黄河之北的下阳城(今山西省平陆县南部),西达今河南陕县、卢氏县,南达今河南嵩县北部,东至今渑池县境,其都城先在下阳城,后来迁都到上阳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区李家窑村一带)。
晋献公时,晋国兼并了临近的许多小国,史称其“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献公不满足于晋国只做一个局限于汾、浍流域的地区性大国,他想渡河南下中原开疆拓土,在晋国南边的虞国和虢国就成为晋国的战略目标。
虢国和周王室的关系比较好,经常和晋国作对。公元前718年,虢国的国君听从周王的命令,干预晋国的内讧,兴兵攻击晋献公的祖父曲沃庄伯,导致曲沃庄伯取代晋君的企图再次失败。晋献公当上国君后,担心自己的同宗子孙学着祖先的榜样,危及国君的宝座,为了一劳永逸,晋献公设计消灭同宗的公族子弟,公族大多被杀,少数残存者外逃到虢国。新仇加旧恨,促使晋献公出兵讨伐虢国。晋国的大臣荀息对晋献公说:“虞国和虢国的关系不错,如果我们攻打虢国,虞国有可能出兵救援,我们晋国要对付两个国家,恐怕很难取胜。虞公是个贪财的人,不如把我们有名的宝马和美玉送给虞公,向虞国借道,以便我们放心去攻打虢国。”
晋献公听说要把宝马和美玉送人,实在舍不得。荀息劝说:“如果虞公得到这两样宝物,肯借道给我们,虢国没有虞国的救援必定灭亡。虢国灭亡之后,虞国也迟早是我们的,这两样宝物能跑到哪儿呢?到时候还得回到晋国来。现在把您心爱的宝贝送给虞国,就好像暂时把房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到院子里一样啊。”晋献公觉得荀息的话有道理,就让他带着宝马和美玉去虞国借道。
晋国向虞国所借的道路,是向南翻越中条山的河东盐池的运盐之道虞坂古道。尽管虞国的大臣宫之奇一再反对,目光短浅的虞公贪图晋国的宝贝,答应借道给晋国。公元前658年,晋军借道虞国,攻克了虢国的国都下阳城,虢国把都城迁往黄河南岸的上阳城。
过了3年,公元前655年,晋国又向虞国借道,再次讨伐虢国。虞国的大臣宫之奇坚决反对再次借道给晋国。虞公根本听不进去,答应再次给晋国借道。这一年的冬天,晋军通过虞国,渡过黄河,攻打虢国的上阳城,虢国的国君逃到了洛阳,虢国灭亡了。晋国的军队在回师途中,顺手牵羊灭了虞国,晋国不仅收回了属于自己的宝物,把虞国的珍宝也一并带回晋国,其中有虞国的“虞侯政壶”,其上的铭文为“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十分具有讽刺意味。这件“虞侯政壶”,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晋国先后灭掉虢国、虞国,南边的边界跨越黄河,河东盐池的运盐通道被晋国掌控,南下中原的通道已经打通;黄河南边的崤山——函谷关通道也被晋国控制,这一点十分重要,等于扼住了秦国的东出之路。晋国通过灭虢、虞之战,吞并了这两个国家,晋献公为后世子孙称霸中原在地缘战略上奠定了基础。
春秋初期,晋国在中原地区的亮相,从跨越黄河作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