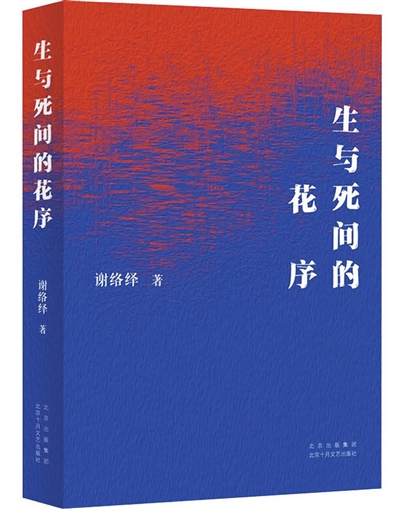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培植自身独有的时空结构,这是一道必做题。谢络绎的小说《生与死间的花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显然是在有意识地生发独树一帜的时序与场域。按照物理学的理论,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二者都是不可分割的,但在作者的书写中,时空的统一性被打破,然后又被重新黏合。
《生与死间的花序》从篇名开始,就暗含了个性化的结构意识。“生”与“死”无疑是小说创作的永恒主题,是对人这一具有悖论性的存在的映射,无论是“因生赴死”还是“向死而生”都不可抗拒地居于无始无终的时间之中,但作者没有停留在对“生与死间”的过程书写,而是一转将这一时间性过程凝结在“花序”这一空间性的排列之中,这个篇名往往会让人误以为是一种语言上的修辞。但即便是如此,篇名其实也暗留了抵达隐喻的通道,因为修辞的本质就是语词如何编织,依旧指向的是结构。
《生与死间的花序》有着自身结构的源代码,这个源代码就是小说目录的构成方式,谢络绎将小说用近乎九连环的方式来编目,并且将其用明显的“1-1”“2-1”“1-2”“2-2”……这样交错的方式来表明。“1”是以“现在”为视点叙述当下指向未来的一个故事,“2”是从当下回溯过去指向现在的一个故事。“1”以“召唤”起航,行至“归位”结束,是一段奥德修斯式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我”与“鲁开悟”互为身影,以一幅画作的完成(消逝)为航标灯,其间伴随着“鲁凌星”步履不停地追赶。各种风格、不同时期的画作穿插在“1”的展开之中,当然,反复出现的以“红蓼”为意象的画作(《红蓼白鹅图》《红蓼蝼蛄图》)构成了其中的关隘。但作者并非要借这些画作本身所具备的意蕴来营造“1”这一部分的文本氛围,她只是将其作为一粒叙事的种籽,与小说中另一个时空里的“红蓼”作结构上的呼应和意义上的关联。相对于“2”中的“江黄”“走马岗”这些固化的村落环境,“1”中的空间场域不断地在变换流转,叙事的重心落脚在时间的催迫之中。“1”这一部分的文本中有读者所熟悉的当下生活的话语模式和世态体貌,大量具有欧化色彩的语言毫无顾忌地倾泻而出,对话与表述之中意见纷呈,一个观点紧接着下一个观点,情感被处理成带有装饰性风格的色点,并毫不避讳地发表艺术评论般的识见,言辞的力度取代了性格的骨架。而当读者一旦进入“2”的部分,就仿佛进入了我们熟知的历史叙事的框架之内,从1940年开始到博物馆的落成,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每一个历史节点都环环相扣。而张银妮也好、鲁红蓼也好,都如土地上的水稻一般扬花、抽穗、灌浆,最后成为田里的稻梗。在“2”这一部分中,每个人物都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动作和语言都涌着一股劲力。在“2”中塑造的世界,气机杂呈,生息绵长,江黄镇、走马岗、鲁湖村人头攒动,泯灭的、腐烂的、新生的和尚存的人和物夹杂此地的土腥和血气,有着强烈的动作性和生命力,此处的景象分外鲜明。与“1”中的语言相较,“2”里面的言辞充满了生活的质感,每个人物都情念奔流,欲念涌动而元气淋漓,一阵阵生猛的气息扑面而来。
“1”和“2”中的语言运用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文本张力。对于读者而言,从“1”进入“2”,在阅读感受上会产生明显的顿挫感,这是作者用一种破坏性的方式在调动读者参与到文本书写之中,它与“期待视野”迥然不同,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求读者把一本小说拆开来读,确实是一种“高维”视角。在此,回到前述阅读小说的完整性建构上,传统的从头读到尾的接受方式仅仅是切入《生与死间的花序》的第一步,如果将“1”串联起来,其间将“2”搁置一旁,再然后将“2”连为一体,又将“1”予以悬置,最后把“1”与“2”再度黏合,在打破、重组之中,一个流变不居的时空搭建起来的叙事迷宫终于露出了它回荡和转徙的面貌。没错,这就是《生与死间的花序》所言的书中书的本相,两本书叠合锁定,对于读者而言,需要类似挑战禁忌的阅读勇气和丝析发解般的阅读技巧才能体会到个中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