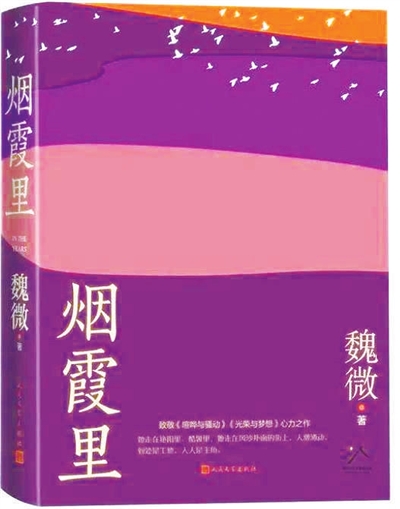读长篇小说《烟霞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突然觉得作者魏微变了。以小城镇为背景,写家庭里的烟火气,写伦理秩序中的爱恨情仇,在无事的悲剧中写出一种难以释怀的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又含着一个游子对故乡、对亲人的眷恋,这是魏微创作的长项,是她小说的鲜明标识,也是很多人喜欢她作品的缘由。《烟霞里》却让人读出了另外一种小说风貌,展现出魏微强大的也是冒险的小说抱负。她执意要突破从前的自我,打破既有的小说格局,写出她的创作理想:为一个小人物撰写编年史,也为一个大时代作记录。人间烟火的挥之不去中,更可见时代风云的潮起潮落。没有想到,魏微会这样处理笔下的人物和故事。
这是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分析和评判。这是一个人人生经历的叙述,更是对社会变迁的直接描写。《烟霞里》仍然有鲜活的魏微小说印迹。一座小县城,与之相关的一两个小村镇。一个乡村女子的成长史。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家庭成员在大善的前提下发生的各种矛盾纠葛与行为冲突。但魏微这一回从李庄这样一个小村镇开始,逐渐扩展到县城清浦,再扩大到地级市江城。地域的拓展也是家庭奋斗史的写照。
魏微在《烟霞里》里直接和历史对话。在小城镇的人物堆里感到舒适的她,突然要评判历史,向时代发问,为未来留下记录。
小说由两个文本构成,一是田庄从出生到成长,从求学、入职到迁徙、成家的自述,在这一自述过程中,打开的是李庄、清浦、江城等乡村、城镇、城市的面貌,是田庄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系列人物林林总总的故事。一是田庄出生、成长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重大的变革。特别是田庄从李庄出发,一路走到她早已心向往之的广东,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微小的生命个体与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时代风云奇妙地结合在一部作品当中,时代风云像巨浪冲击着每一个个体生命,也像一道长城,耸立在每一个个体生命面前。于是小说呈现出两种看上去截然不同的文体。田庄家族的故事依然延续着魏微一贯的叙事风格。小城镇的生活景象,每个人内心并不巨大却很激烈的激荡与冲突。关于时代背景的铺陈,小说从田庄出生的1970年起,以编年体的方式,逐年讲述田庄的生长历程,这种严苛的方式使得小说无可回避地要将每一年的时代背景、重大事件都写入其中。于是,一种“报纸新闻体”的讲述就不时地加入其中,成为小说的“论说”部分。这些背景,基本上是一名小说家在用社会分析和新闻评论的方式,讲述自己听闻、经历以及事后追踪到的重大新闻。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就这样由小说家融入到自己的故事讲述中。我说魏微创作风格的突变,而且是冒险式的突变,就是指这一部分的加入。它们在字数上占有相当比例。
除了对国内国际大事要事的记述、评述,小说还结合田庄的个人职业,叙写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思潮的流变,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现象,以及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的色彩纷呈。就此而言,自叙传的痕迹依然强烈地映照在人物尤其是田庄身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时代背景的交待与小说人物故事发生内在的、切实的关联。
从一个人出生开始的记述,当然不可能以其本人的口吻叙述完成,相当多的部分需要有一个超出角色的叙事人来承担,否则,不是逻辑不通,就是不可能均衡。于是,我们在小说中读到了一个既不是田庄,也不是小说作者的叙述视角。这个叙事者没有身份,不是人物,就是一种笔调,一种假设的、假定的存在。这个叙事视角称作“我们”。这个“我们”具有全局性且超然物外。有的时候,这个“我们”有点像影视剧里的画外音,帮助人们理解人物不能直接说出的内容。比如,说到田庄还叫小丫的幼年时期桀骜不驯的性格,小说写道:“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其实小丫还好。桀骜不驯是有的,但也要看对谁。”这个“我们”是谁?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我们”在小说的开始部分成了必须存在的叙述者,很多说理的内容大都由“我们”来承担。读到小说的结尾部分,这个“我们”逐渐得到合理解释。这就是,所有这些故事,原来是由田庄的几个朋友共同完成的。为了把故事写好,田庄的几个闺蜜还请来了一位叫“魏微”的作家共同完成。“魏微”很愉快地加入到讲述田庄编年史的撰写工作中,并和大家一起讨论田庄人生故事的种种。这是一种叙事策略,也影响了读者对人物故事的认知。当然,这个“我们”在小说后半部分逐渐退隐,这是随着田庄可以自我识别人事、辨别是非而自动形成的。
魏微写作疆域突然扩张,理想抱负陡然增大。我视其为有可能打开新空间的一次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