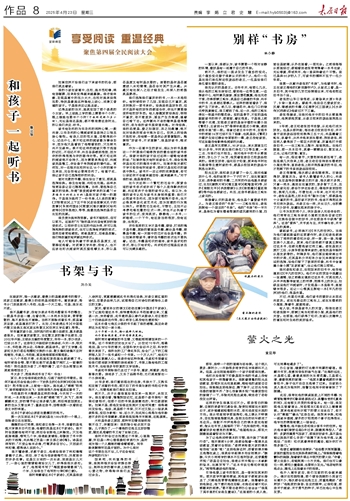刘小云
在娘家时,每一次搬家,最费力的是搬装满书的箱子,成家之后搬家,最费力的依然是成堆的书。搬到新家,将书分门别类排列入书柜,也是一个大工程。可是,我乐此不疲。
我不是藏书家,没有为装点书柜而整套买书的概念,一般是书店逛一圈,左看右挑,一本两本买回来,零零散散的,既不系统也不高端。当然不排除成套买书,那是喜欢至极,或是遇到打折了。比如,《布老虎丛书》《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梁实秋散文》《世界文学名著》,等等。
早年喜欢读小说,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都买,基本都是老版本。后来喜欢读散文,当红散文家的集子也都买,自2002年开始,王剑冰主编的年度散文,年年一本,积少成多,已经20本了。这些年又开始钻研古典诗词,今天一本,明天一本,书柜里、枕头边、马桶旁,都是诗书。进了文学圈,名家和文友们签名相赠和交换的小说、散文集和诗集不定时地增加,书案上、书柜里,甚至角角落落成摞堆放。
七八个书柜不够,衣柜里和顶柜里也都装满了书。有时候我会想,要不要在客厅或是餐厅再打上一面墙的书柜?终归是因为老了,不想折腾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咽回去了。
书太多了,把我养成书虫了吗?非也!
某日,孙女给我讲起史铁生,勾起了我的旧书情结。我何不趁此机会给她分析一下史铁生的《合欢树》和《我与地坛》?把书抽出来,上面有一层灰。她在桌上“啪啪”拍两下,居然能看到灰在飞!说明我很久没有重温这套书了。
书柜里的书大概都是这样的待遇,今天用了一天的时间,一本本抽出来,一本本都“啪啪”两下,灰飞了,我再翻翻内文,好的情节会让我多看几眼,然后再放回原处。新的念头又冒出来了:重温这些书,回想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字的味道。
这本《千家诗》必须放在最醒目的地方。
第一次见到这本《千家诗》是在1984年的一个晚上,我陪老父住在医院。
幽幽的台灯两侧,我和老父各捧一本书,我看的是电视大学课本古代汉语,他看的则是这本《千家诗》。我不时会观察他有何不适,然后会安排他上床睡觉。只见他起身倒墨,想写几个字,我便赶紧铺纸,却瞟到了书中所夹的干枝梅,而夹梅之页是一首王淇之诗《梅》。诗是这样写的:“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
我不懂诗意,求教于老父,他便给我讲了林和靖梅妻鹤子之典。然后,讲了他与母亲青梅竹马、共度艰辛的许多往事。这是父女间的一次长谈,到底是女儿大了,一些心里的情愫能倒给女儿了,听得我泪水滂沱。末了,他挥笔书写了“梅姐爱吾情最深”几个字,又给我念了他写的七律《悼亡妻》。
我时常翻看这本《千家诗》,尤其是我进入诗界后,更愿意翻阅此书而消化经典,对老父画红道的诗句,总要多品味几次,试图将自己对诗句的感悟合上老父的文脉。
某天,看到孙女的课文《依依往事》中提及《千家诗》,为了让她知道这本书,我特意将其从书柜里请出来,又重温一次,突然看到,此书竟然是以唐代末期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详注作终,我以前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
这本价值七角五分钱的书引起了我的感慨,吴定命老师还为此写过一首小绝:
三十年前一本书,梅心揉碎几回枯。
而今重拾深层意,不许悲情再复初。
我时常对着满屋的书生情,又想起刚刚请回来的一个书架。这个书架的历史也太长了。20世纪70年代,准确地说,是1978年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我所在的工厂借此东风,给全厂上下的工程师每人发了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一个万人大厂,有此行动也确实鼓舞人心。我老伴有这种待遇,书桌和书架着实给我们那间极为简陋的房间添彩了,书架上既有他的工程技术书,也有我多年积累的文学经典。
书桌和书架陪我们走过了十多年,搬家,再搬家,地位渐渐次要。房间多了,又买了品牌书柜,它们就被留在一个小房间里。
20年多前,我们搬到现在的住房,书房大了,又购买和定制了成套的书柜,那只旧了的书架与新的书柜似乎格格不入,无情地被我们淘汰在旧居。
前不久,次子从微信里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未加文字。我左看右看,慢慢找回记忆,这是那个老书架吗?框架似曾相识,但那个旧的书架是黄颜色的,早已斑斑驳驳。如果不是,那他发给我这张照片又有何用意?我将疑问发给他。他说,就是那个书架,只不过又贴上一层家具装饰纸,变旧为新啦!哈,这小子,如此用心地将与他年龄差不多的旧书架翻新,那装饰纸贴得平平展展,还挺漂亮。
大约是年老之原因,那种怀旧情结居然控制不住了,快搬回来!我的指令有点刻不容缓。儿子照办了,一个墙角的空地正正好好摆放,随处乱堆着的书又有了安居之处。
我时不时会过去抚摸这个书架,心里揣摩,怀旧是一种心理现象和审美行为,是时间为每一个人酿制的醇香葡萄酒。用年龄来解释怀旧是片面的。为什么我对这个书架念念不忘,儿子还会有这种亲昵的行为?
回来吧,失而复得的书架,我照样每天会给你拂去浮尘,照样在你的腹中装上我的心爱之物,你将陪伴我们走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