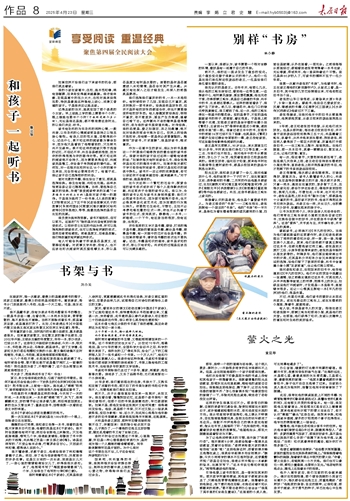黄亚琴
那年,我带一个班的道德与法治课。这个班人数多、课时少,一开始很多同学的名字我都叫不上来。但是,坐在班里角落的一个孩子却惹我注意。
他初次给我留下印象是因为他的书桌上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摆着课本。我踩着清晨的阳光走进教室,粉笔灰在光柱里起舞,唯有他的桌面空空如也。我轻轻走到他身边,蹲下身子,让目光与他低垂的眉眼平齐:“怎么没拿课本呢?”他像受惊似的瑟缩了一下,手指死死抠住桌角,喉结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这样的学生我遇见过不少。那些苍白的辩解、空洞的承诺早已教会我,指责如同落在水面的石子,或许能激起短暂的水花,却无法改变水流的方向。我从邻座同学那里得知,他上课从不带课本,总在抽屉里捣鼓玩具,连班主任的训斥都成了耳边风。我默不作声地将自己的课本放在他面前,指尖在书页上轻轻叩了叩:“先用我的吧,书里藏着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呢。”他猛地抬头,那双大眼睛里盛着惊讶与不解。
为了让他养成带课本的习惯,我开始了“秘密行动”。每天课前5分钟,我都会抱着一摞课本走进教室,笑着对全班说:“老师来检查大家的课本有没有‘迷路’啦!”走到他身边时,若看到课本端正地摆在桌上,我就会举起课本向全班展示:“瞧瞧,今天小雨同学的课本不仅准时回家,还穿戴整齐呢!”若是空空如也,我便从怀中掏出一本崭新的绘本,在扉页写下:“这本书说它想和你做朋友。”再悄悄塞进他的抽屉。
引导他爱上读书的契机,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雨。那天放学时暴雨倾盆,其他孩子都被家长接走了,只剩他孤零零地蜷缩在走廊。我撑着伞走到他身边,他下意识地往后躲,衣角还沾着不知从哪蹭来的泥渍。“要不要去老师办公室坐坐?”我晃了晃手里的《安徒生童话》,“这里面的小美人鱼,可比雨幕有趣多了”。
办公室里,暖黄的灯光晕开雨雾的潮湿。我翻开书页,故意用夸张的语气念道:“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他原本攥着裤脚的手渐渐松开,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凑了过来。当读到小美人鱼化为泡沫时,我瞥见他用手背偷偷抹了下眼睛。
此后,我常在他的课桌里放上不同的书籍:充满冒险精神的《鲁滨逊漂流记》、温馨治愈的《夏洛的网》,还有图文并茂的科普绘本。有一回,我发现他正皱着眉头,用铅笔在《昆虫记》上圈圈画画。原来他被法布尔笔下的萤火虫迷住了,却不认识“鞘翅”“磷光”这些生词。我找来字典,和他一起逐字查阅,窗外的夕阳把两个影子拉得很长,他专注的侧脸被镀上一层金边。
慢慢地,他开始主动和我分享书中的世界。有次他举着《绿野仙踪》冲过来,眼睛亮得惊人:“老师!多萝西靠勇气回家了,那我好好读书,是不是也能让妈妈不那么辛苦?”我蹲下来与他平视,认真地说:“当然!知识就像神奇的魔法,能为你打开很多扇门。”
他曾红着眼睛向我倾诉:“爸爸整天浑浑噩噩,家里的重担全压在妈妈柔弱的肩上。”我轻轻搂着他颤抖的肩膀,指着窗外草丛中明灭的萤火说:“你看,萤火虫虽小,却能照亮一小方天地。我们也可以像它一样,哪怕力量微弱,也要努力发光。”他若有所思地点头,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
他升入高年级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偶尔在校园相遇,那个曾经畏缩的小男孩已长高不少,每次都会远远地立正,郑重地鞠躬:“老师好!”他挺拔的身姿、坚定的眼神,让我知道,那些关于阅读、关于勇气的种子,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