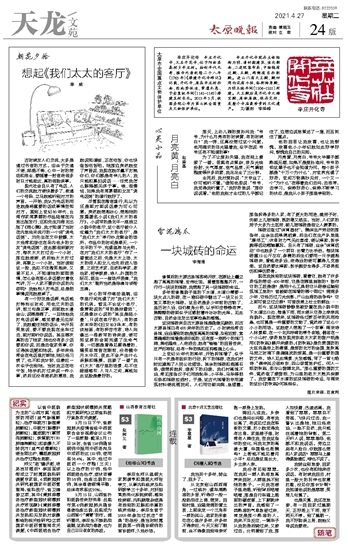修复后的太原古县城即将开放,在原址上矗立起了高高的城墙,宏伟壮观。看着那整整齐齐,一行行一块块的城砖,我想起了另一块城砖的命运。
多年前修整院子里的下水道,水道口需要一块大点儿的砖,在一堆旧砖中翻出了一块又长又宽又厚的大城砖。这自然是多少年前的古物了,虽历时久远,但仍棱角分明,以手叩击铮铮有声。黑黝黝的砖面似乎还散射着冷冰冰的光泽。见此古物,自然会生发出世事沧桑的感慨。
这块城砖来自古太原县城是确凿无疑的,而古太原县城已有600来年的历史了。小时候经常去县城,远远看到的就是那高高的城墙,及到近前,宽厚巍峨的城墙是须仰视的,还有那一连两个的城门洞,黑咕隆咚,人走进去,就有“嗡嗡”的回音传来,庄严而神秘,总有一种恐惧和压抑感袭上心头。
上世纪50年代的某年,开始拆城墙了,似乎只有一次是有组织的行动,拆下的城砖,在我们村附近建起了人民公社猪场。其余的城砖和根基石条,谁想拆就拆,谁拆下的归谁。我们村离城不远,常见那些汉子们用独轮车、小平车、马车等把石条和城砖拉进村。于是,这古代城墙的专用建筑材料便流落民间。人们用它砌鸡窝、垒猪圈。那些拆得多的人家,有了更大的用途,盖房子时,先砌上几层城砖,既防潮又结实。当时,人们家的房子大多为土坯房,砌几层城砖是很让人羡慕的。
城砖还做过“体育器材”。集体生产劳动的那些年,业余生活单调枯燥,后生们在生产队地里“磨洋工”,休息时力气无处宣泄,便以摔跤、扳手腕等活动赌输赢玩。自从有了城砖,业余“体育活动”中也就多了一个项目:比臂力比手劲。每块城砖重12公斤左右,参赛的后生们要用一只手提起城砖来,看能走多远,走得远的便可赢得几支香烟。这自然要比摔跤、扳手腕安全得多,不容易扭伤和摔伤筋骨。
现在我找到的这块城砖,看着它,就有了许多奇怪的想法:600年前,它是在哪里烧制的?制作它的工匠是谁?是用什么工具把它从砖窑运输到筑城工地的?曾被砌在城墙的哪个部位?绵绵多少年,它经历过刀光剑影、尸山血海的战争吗?它上面可曾立过云梯?可曾泼溅上壮士的鲜血……
而今,这块城砖静静地被安置在我小院中的下水道出口处,每逢下雨,雨水便从它身上淙淙流向院外。现在想来,这城砖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也可算是一件重要的文物了,竟然派了这么个小小的用场。这就使人想起了一个故事:南宋诗人林景熙,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冬夜晚,借宿在一个小山村,惊奇地发现房东老太太家的窗户纸是用《防秋疏》撕开来糊的。《防秋疏》是负责国防的大臣向皇帝上的奏章,是预防北方的金国,趁秋高马肥之时南下侵袭骚扰的预案,是一份重要的国防文件。诗人见此情景,大发感慨,写了一首七绝诗:“偶伴孤云宿岭东,四山欲雪地炉红。何人一纸防秋疏,却与山窗障北风。”那么重要的国防文件,竟然做了糊窗纸,为山里的老太太挡风保暖了。我安置在下水道的这块城砖的命运,与南宋的这份《防秋疏》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