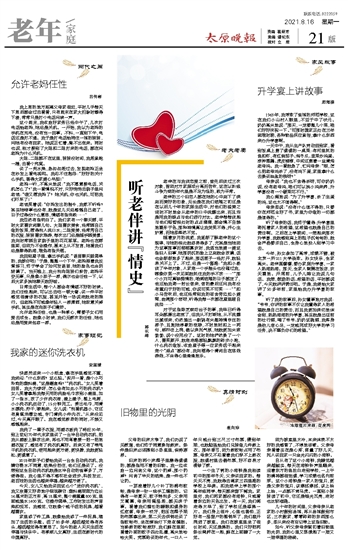父母的旧床太窄了,我们劝说了无数遍,他们终于同意换张新床。条件是旧床必须挪到小卧室里,保持原样。
旧床的两个床箱子里塞得满满的,都是些用不着的旧物。我一边收拾一边问询父母,这个扔掉、那个扔掉?问询了半天的结果,是一件也不让扔。
一顶挂着好几个补丁的棉布蚊帐,是母亲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的。记得有一年夏天,蚊子特别多,父亲用艾蒿熏,母亲用蒲扇赶,都无济于事。看着我们惺忪的睡眼和满身的红疙瘩,母亲一咬牙,把压在箱子底的布票拿出来,第二天去供销社买了些蚊帐布,坐在煤油灯下连夜缝制。当崭新的蚊帐挂好,我们躺在里面,看着外面的蚊子四处乱撞,高兴地哈哈大笑。凭票购买的年代,一口人一年只能分到三尺三寸布票,攒到年底,也就勉强给我们兄妹做几件新上衣。那年春节,因为新蚊帐占用了布票,母亲又不忍看着我们穿不上新衣服,就满村里去借布票,好不容易才凑够了数。
一个生了锈的小闹钟是我刚读初中的那年冬天,父亲买回家的。每天天不亮,我就得去离家三四里路的学校上早课。和我结伴上学的那个高年级同学,每天都来窗下喊我。家里穷,我们两家都没有闹钟,只能看着东边的天色出发。有一天,我们俩走得太早了,到了学校还是漆黑一片。我们身上很冷,心里也害怕,正好有一扇窗户的插销坏了,我们推开爬进了教室。我们在教室里坐了很长时间,天还是黑的。我们只好把两条长凳拼在一起,躺在上面睡了一大觉。
因为教室里太冷,本来体质不太好的我感冒了,不停地咳嗽。父亲母亲看着实在是心疼,商量了好几天,托人买回家一只金光闪闪的小闹钟。
自从有了这个小闹钟,我睡觉越来越踏实,每天在闹钟铃声里醒来,迎着东方的鱼肚白走到学校,一上午的精神都很饱满,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这个小闹钟是一家人的宝贝,更是父亲的宝贝,该擦拭擦拭,该上油上油,一点都不肯马虎。一直到小妹妹读了初中,它还是锃光瓦亮,走时也比较准确。
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母亲从老家的小村搬到县城,再从县城搬到市区,三次搬家,零零碎碎的东西那么多,却从来没有忘记带上这些旧物。
如今,听父亲母亲絮叨着旧物里的光阴,我的心里又荡漾起了一层又一层幸福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