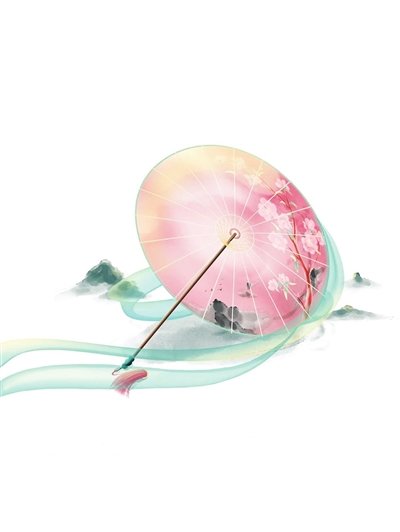下雨天,家长们像约好似的,都阻止我们去上学。常常是午后睡一觉,迷迷瞪瞪睁开眼,外面雷声震天,大雨瓢泼。不用上学也不很高兴,趴在窗前看雨,院子里成了麻河,鸡们躲在屋檐下,一条腿蜷在腹下,闭着眼打盹儿。夏天,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响雷一声比一声远,雨点一滴比一滴小,小孩拽顶草帽往头上一盖,跑到场院看河。温河照例在发大水,小孩兴奋得不知所以,将草帽扔到半空中,比赛谁扔得高,接得准。一不留神就扔到大人脸上了,刚想喊声叔叔大爷,却发觉是大头大脸的老师,吐吐舌头,背过身,做个鬼脸。
家里多了一种透明塑料袋子,正悄悄取代麻袋和布袋。大人们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等到下雨,将两个角套在一起,正好是个帽子的形状,这就是我们的雨衣。这种雨衣,我穿了三年。为了更安全,雨衣外面还戴一顶草帽。班里四十几个同学,都是这样的行头。
直到上班以后,夏天工厂发福利,才拥有第一把黑色尼龙长柄伞,高兴得呀,舍不得撑开,怕破坏了那些好看的皱褶。我妈爱惜地用头巾裹好,又拿布条绑了三道,放在柜子最里面,当宝贝供着。
祖母说,她是见过雨伞的,那是她很小的时候。雨伞是用漆布做的,伞骨是木头的。天热的时候,私塾先生穿长衫,打着伞,臂弯里夹一本书,穿过柳荫下聒噪的蝉鸣,款步而来。雨伞这物件,似乎更适合书里、戏里、电影里。比如白娘娘撑一把“清湖八字桥老舒家做,八十四骨,紫竹柄,不曾有一丝破”伞,在台上碎步轻摇,水袖挥舞,眼光流动。那一刻,这把桐纸伞,就该是许仙的惊魂一刹,高声咿呀的狂喜。也是诗里那个姑娘最好的依附和衬托,好似没有伞,她便只能急慌慌地东躲西藏,哪有闲情逸致去结丁香之愁?
雨伞普及是后来的事。街上的人们撑着规格、颜色、质地一样的黑雨伞,偶尔遇见有人撑把折叠伞,羡慕不已。有年去西湖,见到一种缎面的平伞,淡色底,上面点缀一些花鸟,看了好久,到底是走开了。
伞是不送人的,伞、散同音。我虽不信,但有次朋友来看我,正好下雨,等到天黑,雨势还不减,她家里又有要吃饭的孩子,无奈拿一把伞出来。她说,这伞是借的,不是送的。借的就会还,会还就会见,会见就不散。好。
在KTV点了首《踏着夕阳归去》,甫一起头,大家便都来唱,“远远地见你在夕阳那段,打着一朵细花阳伞,晚风将你的长发飘散,半掩去酡红的脸庞……”往日时光,点点滴滴,纷纭而至,眼底胸下,炙热一片,仿佛热炉沸水,恨不能溢倒出来。唱完良久,不能自已。旁边的孩子感慨道:你们那时的歌原来这么好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