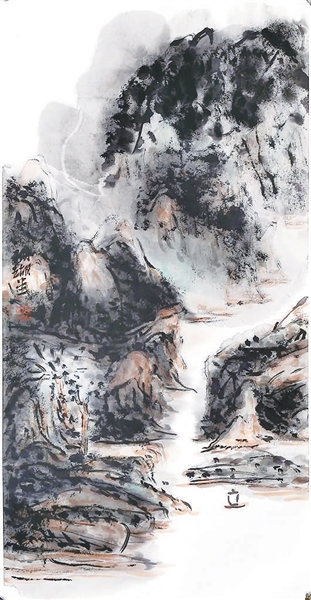祥夫老师是位高产的作家,每年都有高质量的作品发表。我读大学时初次接触到他的作品,是他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上边》。那时我的阅读经验有限,对小说的理解也简单,认为小说就是讲故事,读小说就是读故事。因此,在读到《上边》时颇为吃惊,心底盘亘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天呐,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吗?没有故事的小说还是小说吗?
《上边》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幅针脚绵密的刺绣,绣的却不是诗情画意的江南,是粗粝的晋北山村。这粗粝又是暖调的,作家用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触,不动声色地叙述了一对固守村庄不愿搬迁的老夫妻的日常,极具生活质感。读这种小说是需要一点儿心力的。在我看来他的小说都是精致的艺术品,近乎于晶莹剔透。
后来又陆续读到祥夫老师的《婚宴》《我爱臭豆腐》《五张犁》等,全是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尤其是那个《婚宴》,让我不忍释卷。
这么说,似乎祥夫老师是位不爱讲故事的作家,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不仅爱讲故事,还总是能把故事讲得妙趣横生,尤其是他的那些中篇小说,像《风月无边》《一粒微尘》,其厚重程度不输长篇。祥夫老师的中篇小说新作《西北有高楼》(《长城》2024年第2期)亦如此,讲述发生在一个单位大院的故事,尽管故事背景是城市,但底色却是乡土的。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从女主角大妞家的第一次变故,一直到大妞的孩子丢失的11年后。时间像一条藤蔓,情节是藤蔓上的瓜,安排好这些瓜的位置,体现了作家对节奏的掌控能力。故事里大量充斥着意外的转折,转折之中又让人感到苦涩、沉甸甸的。
在塑造人物方面祥夫老师很有自己的一套,无论是作品中的核心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三言两语,形象、情态便会跃然纸上,既真实粗粝又妙趣横生。
许锁凤恐怕是《西北有高楼》里塑造的最成功、最立体的一个人物。许锁凤的丈夫王大义有个口头语——“世界观”,因为总是把这个词挂在嘴上,人们背地里都喊王大义“世界观”。许锁凤和王大义都是极具正义感的人,这夫妻俩真是心性相通。王大义去世后,许锁凤便从亡夫那里接续了这句口头语,无论是开心还是生气,总是把“世界观”挂在嘴角,慨叹着:“我的世界观变喽,我的世界观变喽……”许锁凤是个极具热心肠的善良之人,要不是有她和王大义帮衬着,大妞可能不会一直熬过来。有魅力的是许锁凤也有“霸道蛮横”的地方,这表现在处理大妞和李红旗的那件事情上,她教大妞诬告李红旗。恰恰是这种正反两面的塑造,使许锁凤这个人物血肉更丰满了起来。
作品中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朱姨。这是个多嘴的女人,多嘴,偏偏又爱打听事,因此,关于这个家属院里的事情,没有她不知道的。通常这种人还爱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这让我想起了冯骥才先生的名篇《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里那个上蹿下跳的小丑似的人物,裁缝老婆。但,祥夫老师笔下的朱姨却不是裁缝老婆的那种坏,她的坏似乎又不是坏,而是性格、秉性使然。虽然就是她的一次多嘴,直接击垮了大妞母亲的生命。这个朱姨的性格又非常丰富,后来她又俨然成为老年广场舞的明星……其他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也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祥夫老师从外貌、语言、语气、神态、行为、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塑造人物形象,同时还擅长使用重复的艺术手法。比如,大妞的标志性动作、许锁凤眼皮跳等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增加读者对这一人物的深刻感受。美国当代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将重复分为词汇、修辞、隐喻等语言成分的重复和事件、情节、人物、主题等故事层面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元素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也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多样化关系。实际上,作品的多重含义恰恰就来自于诸种重复现象的组合。
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祥夫老师很少用心理剖析的方式大篇幅刻画人物心理,而是通过人物对话、独白、行为等侧面描写来暗示人物的心理状态或变化。在短篇小说《上边》里,母亲看儿子干活,自己的嘴巴会一张一合、一张一合,是暗暗给儿子使劲呢,还是在心里感慨着什么呢?作者故意不说透,读者只能自己猜。还有母亲拽过一个盆子把儿子撒尿的地方盖起来,也没有任何心理刻画,这种沉默的爱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西北有高楼》里,祥夫老师依然延续了这种含蓄的风格。例如,大妞生了个儿子,父亲老张高兴,就去商店给女儿买鸡蛋,结果得意忘形,把女儿生儿子的事情告诉了老吕女人,俗话说,守着矮人别说矮话,结果大受刺激的老吕女人连红糖都称不了了,撒了一地。她自己跑到了洗手间半天没出来,还一个字一个字地自言自语:“我让你高兴!我让你高兴!”这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除了妒忌,还会有什么预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靠猜测,人物的意识世界被刻意隐去了,留给读者参与的空间就越大,这和中国古典文学含蓄隽永的美学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悲苦贯穿《西北有高楼》的全篇,最后的温暖来得太突然……祥夫老师的小说就像一条不动声色的河,在什么地方拐弯,什么地方急促,什么地方平缓,什么地方急转直下,最终又流淌到什么地方去,你完全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