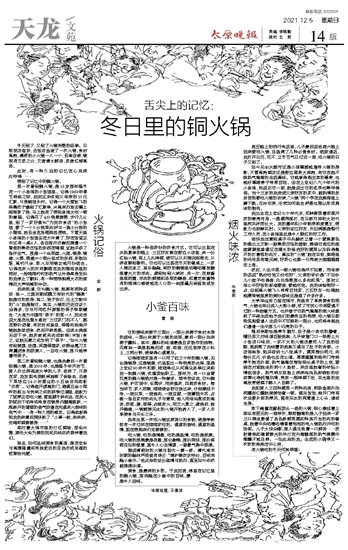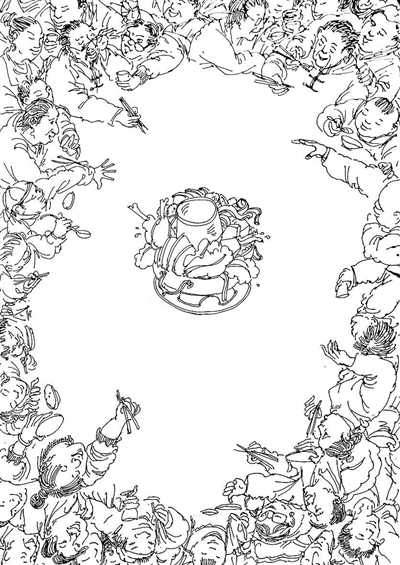金 新
冬天到了,又到了火锅消费的旺季。日前朋友做东,去饭店品尝了一次火锅,食材高档,精致的小火锅一人一个,自涮自便;锅底有文武之分,文者清水鲜汤,武者红辣高汤。
此时,有一种久远的记忆在心灵深处呼唤……
想到了记忆中的铜火锅。
第一次看到铜火锅,是18岁那年隆冬在一个小县城的小饭馆里。记得1969年春节将临之际,我因还未收到父母亲的10元汇款,只身蜗居乡村。记得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终于拿到了汇款单,兴高采烈地去镇上邮局取了钱,马上就有了想到县城大吃一顿的奢望。记得花了4分钱摆渡费,步行几公里,到了一家好像叫“为民饮食店”的小饭馆,要了一个5分钱菜肉饼与一碗8分钱的小馄饨,独自坐在角落狼吞虎咽。下雪天里小县城的小饭馆实在太冷清了,好在饭堂正中还有一桌6人,各自敞开衣襟而围着一个冒烟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喝酒,这就平添了些许生气。那是一个由底盘、火座、锅身、锅盖、火筒、筒盖六个部分组成的东西,形制如塔,高约尺余,取火与用锅功能巧妙结合。记得在炭火的灰烬飘落在我的馄饨汤里的同时,一股隐隐约约的热气让冷得浑身发抖的我停止了颤抖,有一种想挣脱棉大衣的束缚而大声呐喊的冲动。
后来知道,它叫铜火锅,起源有两种说法:其一,三国时期或魏文帝时代的“铜鼎”就是它的前身;其二,始于东汉,出土文物中的“斗”就是指它。其实,火锅的历史应该久远得多,它与巧用杠杆原理的筷子珠联璧合:“大禹为中国用‘筷子’的第一人,民间传说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在野外进餐,有时时间紧迫,等兽肉刚烧开锅就急欲进食,然后开拔赶路。但汤水沸滚无法下手,就折树枝夹肉或粉粢(米饭)食之,这就无意之间发明了‘筷子’。”如今火锅传到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依赖金属刀叉调羹进食的欧美人,一旦吃火锅,那只能学着用筷子。
第二次看到铜火锅,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铜火锅,是2003年,也是隆冬年关时节,爱人外出探视读大学的儿子,夜深了,只身在家,我发现电表跳闸烧断了保险丝,去楼下菜场边24小时营业的小五金店向老板“求救”。记得推开虚掩的门,堆满五金小部件的柜台与货架之间的狭窄过道里,老板为了驱寒正在吃火锅,雪里蕻冬笋肉丝,在炭火的驱动下咕咚咕咚地在锅身内翻腾跳跃,一瓶新开的黄酒的香气弥漫在充满炭火烟味的空气中……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记得老板得知我的来意后爽快极了:“小事一桩,来来来,先喝杯酒暖暖身……”
面对着大城市里的灯红酒绿,废俗兴雅,原先大俗为美的民间风味依然陪伴着我们。
其实,如何品味美食的真谛,是在世俗与高雅碰撞间寻找逝去的自我亦或灵魂的哲理性问题。
小釜百味
景 祺
火锅是一种很奇妙的饮食方式。它可以出现在炎热夏季的晚上:三五好友聚在街边小店里,来一份红油火锅,再上几扎啤酒,便可以从天南侃到海北,从深夜聊到黎明。它也可以出现在冬天的餐桌上,一家人围而坐之,其乐融融,架好的铜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着大片的羊肉。煮到恰到火候时,夹一片,在麻酱里滚两圈,羊肉的鲜美和汤底的醇香,和着芝麻酱特有的绵润口感便能在入口的一刹那毫无保留地迸发出来。
它的美味来源于三部分,一部分来源于食材本身的滋味,一部分来源于火锅的汤底,最后一部分则来源于蘸料。其中,蘸料的味道最是自家制作的独特,花椒油一律是现榨而成,香,浓香,汪汪地浮在小料上,三两分钟,便涮得心满意足。
记得姥姥家里有一口用了近三十年的铜火锅,无论是锅身,还是锅盖,仍呈现出一种明亮的光泽,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姥姥单位从河南兄弟单位采购回一批铜火锅,优惠卖给职工。那年月,有一口金黄瓦亮的铜火锅绝对是一种奢侈。姥爷告诉我,它叫铜火锅,炉芯居中,似筒状,用来装炭,四周放食材。每当年节,家人团聚,姥姥便会把它找出来,仔细擦拭干净,一层白菜,一层烧肉,一层豆腐,一层蘑菇木耳,点缀一些自家炸的肉丸子与青菜,倒入用母鸡熬成的高汤,放葱、姜、枣等,点燃炭火,用文火熬之,煮沸后,掀开铜盖,一锅鲜美无比的火锅开始诱人了,一家人尽享美食与天伦之乐。
我有生第一次吃火锅这样烫口的食物,便是学龄前有一次过年在姥姥家吃的。满屋的香味,满屋的温情,现在想起来仍觉暖暖的。
吃火锅,吃的是情趣,吃的是温情,吃的是氛围。吃火锅的氛围最是有趣,那份酣畅,那份爽快,那份挥洒自如的惬意,直令人心生情愫,一番豪气胸中荡漾。
据说清朝时的火锅与现代一模一样。清代咸丰时期的翰林严辰曾有诗云:“围炉聚饮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他点染的这份温情与热烈,直至如今依然被津津乐道。
美食,是最深的乡愁。于我而言,停留在记忆里的铜火锅,那消融在小釜中的百味,最是令人回味。
烟火味浓
牛茉莉
周五晚上的例行电话里,儿子最后说他周六晚上回来要吃火锅,且强调了几种必备食材。结束通话,我打开日历,可不,立冬节气已过去一周,吃火锅的日子又到了。
如今无论大都市还是小城镇都能遍寻火锅的身影,不管高档酒店还是街边简易大排档,有它在就不缺热气腾腾的生活真味。它能承得起主宾的尊贵,也能纡尊降贵于寻常百姓。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县城,别说见它一面,就是说出它的名字也稀罕得很。当十三岁的我走进父亲好友的家中,被热情的叔叔告知要吃火锅的时候,“火锅”两个字在我脑海里上蹿下跳、左冲右突,任凭如何组合拼凑也难以形成具体的指向。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耳畔激荡着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一路摸爬滚打,在日新月异的大时代里栉风沐雨长大。我的童年和少年物质极度匮乏,想象力也捉襟见肘。父亲的这位好友,夫妇俩都是银行工作人员,在小县城里这是令人眼红的好工作。
很快我注意到桌子中央赫然立着一个黄黑颜色的像出土文物一般稀奇古怪的器物,围绕它周边的盘盘碟碟里盛满还在滴水的择选好的蔬菜以及码得整齐的打着卷的肉片。真实的“火锅”就在目前,脑海里的问号却有增无减,好奇心也像一只爬树大猫蹭蹭蹭往上涨。
然而,人生中第一顿火锅吃得并不如意。用母亲的话说“既没吃饱又没吃好”,父亲的评价是“不如炒几个盘子吃得香,白白浪费那么多肉和菜”。那时父母心中好饭的标准要香,要能吃饱。我的体验稍好一点,但距离火锅飞入寻常百姓家,三五好友一吆喝就能攒局锅里捞的美妙滋味还是差了许多许多。
大学毕业努力留在城市,兜里有了享受美食的底气,火锅也早已流入大街小巷,成了市民心中再普通不过的一种就餐方式。也许缘于它热气腾腾的烟火味像极了平淡生活给予我们的最务实的构想,吃火锅日渐构筑起普通人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也终将串起我们漫漫一生中那几个闪亮的日子。
婚后孕期恰是寒冬腊月,肚子是个贪吃的饕餮,嘴巴却又对味道百般挑剔,几乎尝遍门口一条街上大小饭店口味后,一家不大的火锅店最终入了我的法眼,既抚慰了我味蕾的挑剔又满足了肚子的贪婪。小店很袖珍,统共容纳七八张桌子。蔬菜每份两元,肉每份五元,价格也实在公道。厚厚重重的粗布门帘将寒冬挡在外面,热气暄腾在每张细长桌子的上空,萦绕在对面就坐的两个人脸前。来店里就餐的年轻小情侣居多。热气将女孩脸上深深浅浅色彩缤纷的妆容雾化得妩媚风情,男孩一瓶啤酒下肚,目光里的迷离欣赏便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我和爱人三四种蔬菜一两种肉类,两条烩面外加两罐杏仁露就美美饱餐一顿。酒足饭饱,掀开门帘再次迎接扑面的寒风,竟有无比的爽意漫上心头,通彻全身。
取下搁置在橱柜顶头一格的火锅,细心擦拭着上面似有若无的一层浮灰,眼前翻腾的是儿子回来一家三口围坐摆满了各色新鲜菜蔬和种类齐全的肉的餐桌,就着中央咕噜咕噜冒着泡泡的电火锅热烈开吃的场面。儿子大快朵颐、爱人满足地撮一口鲜汤……放射着柔和橘黄暖光的吊灯在升腾翻滚的热气围裹中微醺不能自持。一如此刻的我。生活的小确幸又一次软软柔柔击中心房。
有火锅吃的冬天何其幸福!
本版绘图:王春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