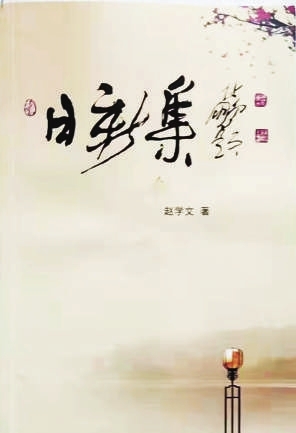今天又想到这句诗,则是因为读了赵学文先生的一本书。书名叫《日新集》,他为了下一步正式出书而自印的一个小册子,俗所谓“稿本”也。引起的感慨,一下子说不清,自己心里明白,是在“人情交往”上。
活了几十年,最易生感慨的,常在这四个字上。有的人,起初还像个朋友,一件小事没顺了心,说翻脸就翻脸,比翻书还快。有的起初不觉得如何如何,打了两回交道,却越来越热火了。跟学文先生的交往,这两类都不是,细想其情形,当是不知怎么就认识了,认识也只是认识了,并没有如何亲密的交往。只是彼此都存着好感,就这么不咸不淡,不远不近地过了好多年。真的,连年数都估摸不出来了。因此上,兴起的感慨,隐约间该是:交往疏阔似寡恩。
这仅是从我这边考虑的,这也是我在与人交往上的毛病。浑浑噩噩就过去了,直到某一天出了事,才知道人家翻了脸或是自己得罪了人。跟学文的交往,虽说平淡,有两件事还是难忘的。一件是多少年前,他组织了个读书会,一次两次都是研读林鹏先生的著作,待我的一本书出来,竟破例为我开了一次,事后还出了白皮的小册子,算是我此生唯一一本他人评论的集子。还有一次,是我在北京赁居以后的事。暑假回到太原,听说林鹏先生搬了家,新家在东山某小区,想去看望,连小区的名字都不知道,找人打听,似乎也有不便。正为难之际,一天学文先生来了电话,说他知道我回来了,肯定未去过林先生的新家,今天他正好有点事带车去林家,问我可愿同行?去了才知道,他连小事也没有,纯粹是为了给我一个方便。
有了这样的回忆,再细捋我的好感,一下子也清晰了。交往是不多,好感则是确实的,一是待人诚恳,二是颇具才情。前者只能说不反感,或者才是好感之由来。我这人,为人寡淡,但有一样与生俱来的美德,就是视才情如美女,只有欣羡,只有好感。
学文先生的才情,我最为欣赏的是书法。在这上头,我俩可说是同道,都是中学教员出身,都是喜爱书法而不以书法家自命。多少年了,他的字一直是“二王”的路子,不急功,也不近利,就那么不屈不挠地写着,在我看来,已然有味了。
有了微信以后,不时翻翻朋友圈,又让我发现了他的另一个才情,文章也写得好。短,有趣。不光有趣,还有品。读了就能记住。记得看过一篇写他上小学当“红小兵”的事,有趣,也沉痛。还看过一篇说“借火”的事。他和司机去了某地,天冷,车熄了火,要借别的车的什么才能打着火。借他火的小伙子默默地做了,连个谢字也不愿意领受。只在他起初开口时说了句:“你怎么知道我有?”我看了觉得,能写得这么干净,不是修炼,而是天分。
料不到的是,前十来天吧,他竟将这本《日新集》寄来了,里面差不多全是他在朋友圈里发过的,且全是繁体字。微信上我问他,就这么出吗?他答了,说出时会转换的。我当天就看了十几篇,其中就有当“红小兵”那则,还有“借火”那则,与其他两则合为《杂记三则》。看了总想写点什么,怕过后忘了,就将刚刚看过的一点想法,潦草写在扉页上。真要写了,会全面些,但我觉得,不管正式写时会写什么,这点最初的感受,是不能缺了的:“散文作家要担起史官的责任,洞察世相,以补正史之疏漏。他们的文章不应当叫文,而应当叫笔,笔者,秉笔直书也。若失去这一秉赋,只是依时献唱,循规作文,文学史上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此语非敢与外人道,且说与学文兄,聊博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