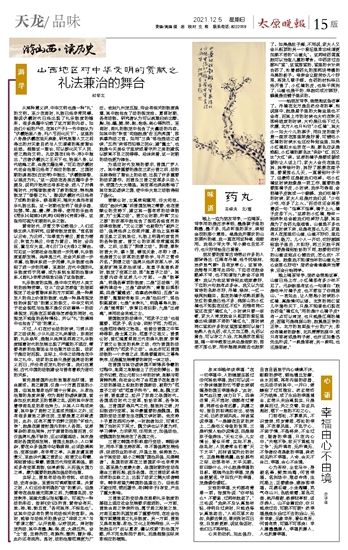黄帝时代,尽管文字记载很少,人们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但黄帝制定官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如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同时,设四臣,置左右大监,有《云门》《大卷》之舞曲。可见这一时期社会治理进一步完善,礼乐制度逐渐发展。尧舜禹三代,社会关系进一步丰富,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礼乐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至周时,古代中国的礼乐制度终于完善,成为系统全面的治理体系。《周礼》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这些制度。
礼乐制度的实施,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它从“应该怎样做”的层面规定了社会管理体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激发人的向上价值的制度,也是一种具有规定性的体现“法”的意义的条文。中华文明关于社会规范与治理不是仅仅依靠单一的法律规定,而是在正面倡导怎样做的同时,也规定不能做的各种情况。所以“礼”的精神中也包含了“法”的意义。
不过,人们在讨论法的时候,习惯从法家之法谈起,少从礼法之礼来看法。东周时期,礼乐崩坏,是指从尧舜至西周之礼乐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需要有新的治理观念与治理方法出现。法家于是应时而现。实际上,中华之法隐含在中华之礼中。法家的实践只是更强调法的意义而已,并没有否定礼的价值。我们注意到,古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与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晋国所处的地理政治环境。晋由唐成。周之唐国,仅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但其地理政治环境十分复杂。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来看,作为周封的诸侯唐国,曾参加反抗周武王的管蔡之乱,说明其中存在着悖周乱世的政治势力。从其人口构成来看,其中除了周封之王室成员随从之外,还有很多唐地之原住民,主要是夏之后裔遗民。此外,还有不属于农耕之民的“怀性九宗”,就是在唐晋封国内的狄人各部。这样复杂的政治局势,对于唐晋的治理而言,仅仅强调礼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法。其次是周时各国竞相发展。晋国土地狭小,人口复杂,要在众多强国中站稳脚跟,必须励精图治,变革创新,有非常之举。从唐叔虞至晋燮父,至曲沃代翼之晋武公,到晋文公称霸,再到晋悼公复霸,晋国历代均变革图强。期间多有变革周制,创举新规,从而强大国力之举。最为重要的就是加强法的治理。
实际上,晋地有法治的传统。依法治法,史有余脉。至晋则可谓顺理成章。炎黄之时,人们还没有明确的“法”的意识。但是黄帝在战胜蚩尤部族之后,为震慑乱民,安定秩序,画蚩尤像以张贴警示。可视为一种法的形态。按照《史记》所言,黄帝设有天、地、神、袛、物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这其中应该有负责与司法相关的官职。尧时,能够与法相关的是设立“诽谤之木”与“敢谏之鼓”,以开言路,以纾民扰。舜时制定刑法,其中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设“士”官,主持刑罚,有膑刑、黥刑、鞭扑等。此外还有流刑。禹时,法的治理范围更为广泛。他划九州定五服,均设有相关的制度典章,其中就包含了法的规定性。夏商时期,各有法制。研究者认为可以梳理归纳出黥、劓、刖、醯、脯、焚、剔、炮烙、剖心等刑罚。至周时,周礼的制定中包含了大量法的内容。如其中的“秋官”司寇就是“佐王刑邦国”,即执掌刑法之官。如用“三典”惩治违法之诸侯;“五刑”来惩罚犯罪之民众;建“圜土”,也就是今天类似于监狱或看守所之类的建筑以教育不良之民等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法治更为健全。
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晋国广罗人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三家分晋之后,法的实践得到了理论上的总结,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法家著作。而晋及三晋之变革多从法入手,使国力大大增强。其变革也深刻影响了其它地区诸侯之国,使中华大地之法制得到了强化。
晋献公时,士蔿受到重用,任大司空。适应“曲沃代翼”后晋国发展之需要,他在晋献公的支持下,建立其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为“士蔿之法”。晋文公时期,所谓“文公之教”的改革中就包含了规范各级官员的法律性制度。“文公之教”也被称为“被庐之法”,强调经济上农商并重,政治上坚持尊周王室之正统地位,礼制上明确约束官员的各种制度。晋文公的改革非常重视郭偃。之后,出现了“郭偃之法”。郭偃,春秋时晋大夫,掌卜筮,善观天象,亦称卜偃。他是晋文公改革的主要助手,与齐之管仲齐名。“郭偃之法”强调从经济改革入手,再逐渐扩展至政治领域。赵宣子赵盾执政时,制定了变革之法,即“赵宣子之法”。其主要内容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制事典”,明确各事项的制度;二是“正法罪”,完善刑律法令;三是“辟狱刑”,清理旧弊积案;四是“董逋逃”,追拿逃佚罪犯;五是“由质要”,整理财务账目;六是“治旧污”,惩治积案腐败;七是“本秩礼”,明确尊卑礼制;八是“续常职”,恢复已有旧职;九是“出滞淹”,举用社会贤能之士。
晋国制定的法律中,“范武子之法”也很重要。范武子,名士会,因封于范,为范氏,也是范姓得姓之始祖。他曾任晋国之中军将等职,是士蔿之孙,范宣子之祖父。晋景公时,曾汇编夏商周三代的典礼制度,恢复了晋文公制定的执秩之法,作为晋国的法度,被称为“范武子之法”。由此亦可见晋国法制的一个矛盾之点,即是要重周礼之尊卑秩序,还是重发展需要的君民一体之法。
在晋国与其它诸侯国不断博弈争霸的过程中,赵简之赵鞅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513年的时候,赵鞅与荀寅铸刑鼎,向社会公布了由范宣子在赵宣子之法的基础上拟就的晋国新法,被称为“范宣子之法”或“范宣子刑书”。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室虚立,拉开了东周之战国时代。各国适应时代之变革,纷纷改革,各争其强。三晋国家得风气之先,据地利之便,对旧制进行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魏国。魏国的变法主要发生在魏文侯时期。他支持卜子夏在西河办学,一时就者如云,可谓汇集了当时天下英才。魏文侯也以子夏为师,学习儒学,力求致用,任用贤才,加强法治,使魏国的发展走在了各国之先。
三晋之韩国亦积极推行变法。韩昭侯时,用申不害主持改革。申不害强调发展经济,促进农业的丰收,开垦土地,保持地力。由于其变法,弱小之韩国“国治兵强,无侵韩者”。赵国的改革在三晋国家中也非常突出,甚至是力度最大者。战国时期的变法浪潮由三晋而起,波及各国。在三晋法家卓有成效的实践之上,出现了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韩非希望为韩国的强盛出力。但他却不被任用,愤而著书,有《韩非子》存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晋地区的变法是在周朝礼乐制度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的。一方面,晋地由周之宗亲所治,属于周之股肱之地,对周王室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治理方面遵循周之礼乐制度。另一方面,晋地又具有地理、政治、文化上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就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并不完全拘泥于周礼,而是根据实际采取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