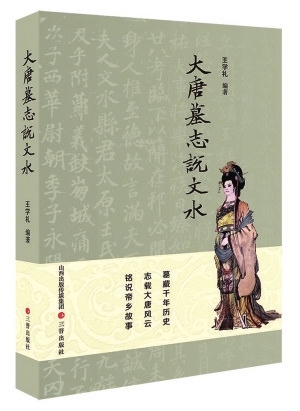从这本书中,我领教了王学礼搜集梳理资料的功力。
从2022年起,王学礼又开始了自己新的追求,搜集到有关武则天和文水县的120方墓志铭,结集成55万字的《大唐墓志说文水》(三晋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赵学文先生在《序言》中说:“随着镌刻在嘉石上的文字而鲜亮灵活。墓志铭也因此成为正史的补充、历史的见证。”“作为丧葬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与墓主沉埋于地下的墓志铭,虽历经千年尘封,出土后其光华依然顽艳夺目,金石不朽……”
文水一向被誉称“子夏寓地、则天故里、胡兰家乡”,王学礼的《大唐墓志说文水》一书不仅延续了他搜集资料的功力,而且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充分发挥地域的优势,由点及面,获得跨越时空的极佳视角。
墓志铭是生者对死者的盖棺论定,也是死者向生者发出的遗言古训。墓志铭正是逝者穿越时空向生者、向人世发出的声音。陵墓中发出的声音无须造伪,言之凿凿的墓志铭不容朝令夕改,字字句句铁证如山。王学礼从丧葬文化中,挖掘出大唐盛世丰厚的历史和时代内蕴。
还是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透过墓志铭,探讨死者的“临终心态”:有“坦然接受”型,有“无憾而卒”型,有“视死如归”型,有“抱憾而终”型,有“悔恨不已”型,还有“怡然待终”型、“忧愁不寿”型等,大千世界,千人千面,心态万相。
墓志铭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写照,也反映着某种生死观,还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认识与主观判断。
王学礼的《大唐墓志说文水》一书收集的120方墓志,一是有关唐代文水县令、县尉、主簿以及处士、其他文水人的墓志;二是武则天家人、侍臣等与武则天紧密关联人的墓志;三是属于文水武氏族人、后裔的墓志。每一方收录的墓志,都包含拓片影印、志文校录、墓志解读三部分。
墓志铭是对死亡的凝视,是对生命的眷念和回顾。
墓志铭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视为一种文体。志者,记也;铭者,名也。无论古今中外,均有“纪念碑性”。按照中国几千年积淀形成的文化观念,一个人无论一生怎样穷困潦倒,命运怎样坎坷沉浮,最后只要赢得个“保持晚节”“善始善终”,走得风光体面,人们也会给他一个“不枉此生”的定论。
墓志铭总是以逝者的生命经历为创作因缘,它在宽泛的意义上讲,不妨看作是一个人的生平传记。从古至今,大量墓志铭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记载和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人物的个体生命价值和当时社会的民俗风情。
墓志铭的表相,再现的是逝者的面容,而铭文则是被斧凿活化的声音。
《大唐墓志说文水》收录的都是唐代墓志,但王学礼把隋代墓志关于子夏山的信息放在了首篇。孔子高徒子夏在文水隐泉山设教讲学,于是有了“子夏遗称”“僧光旧迹”的摩崖石刻,以此篇作为开卷,隋启唐承,让人尤觉编纂者独具匠心。
王学礼在搜集上颇下了一番功夫:既有在文水境内出土的一些墓志,也有从洛阳、西安、佛山等地书商手中购买的墓志拓片……以至赵学文读后感慨万千:“顿觉那些冷冰冰的志石此时似乎有了温度,好像志主和我们在作千年对话。唐代文水的历史风云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而是不同地位、身份、性格、经历的人的命运跌宕的生动再现。”
墓志铭还包含了“生死两茫茫”,阴阳两界由此隔空喊话:逝者在生前说话,却明知它在其死后被阅读;抑或由生者想象,死者生前未曾吐露的心理潜台词。总之,这是一个虚拟的、跨越生死的言说行为。
从墓志铭里,后人还能够看到,生死临界之际,当赤裸裸灵魂无奈离去之际,人之初的“粉墨登场”到了曲终灯暗的“卸装时分”,在此生离死别的时刻,无疑会袒露内心的纠结和矛盾。
我小时候,看《冰山上的来客》,有句话一直不懂。侦察兵把古兰丹姆救出来,自己中了黑枪,临死前,古兰丹姆对死者说:“记住我,我叫古兰丹姆。”活着的人竟然恳求死者记住她,岂不是匪夷所思?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我懂了。活着的人对生命总有亏欠,面对死而无憾的逝者,能把活着的人带入历史记忆,乃是一种奢求。面对墓志铭,我们往往会产生生死纠结:有些人虽然走了,但他永远活着;而众多活着的芸芸众生却如同行尸走肉。墓志铭成为映照人生的一面镜子。
墓志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是生死两界的沟通和互动。
赵学文先生在序言中说:“墓志铭研究是一门学问,因其难而涉足者稀……单方的碑拓微不足道,众多碑拓做系统整理,便是学术研究的瑰宝。”
感谢王学礼先生用精彩的书写让读者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