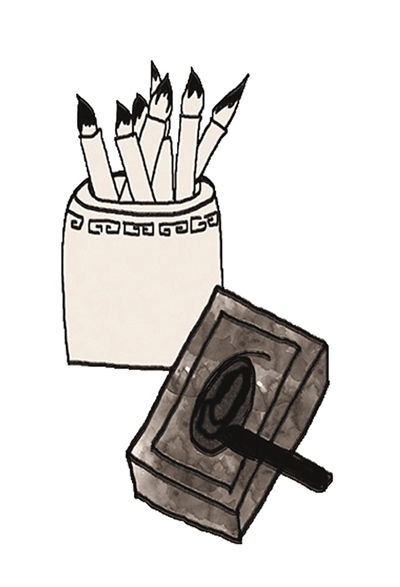其一,读书需博闻强记,而且要在记忆力旺盛的弱冠年华多读多背多记,不断积累、积淀。他曾为子侄讲述自己青年时代强化记忆的故事。弱冠时,尝与家中西席马生较劲记性,以53篇文章比试。结果年长的马生一天下来仅背得四五篇,自己一早即35篇上口,而且不爽一字。傅山以此告诫子侄,并非自己天资高于西席马生,“此时正是精神健旺之会,当不得专心致志三四年”,“然如此能记时,亦不过六七年耳。出三十则减五六,四十则减去八九,随看随忘,如隔世事矣”。这是傅山先生读书与治学实践的体会,一个人最佳的记忆年龄也不过五六年,一旦误过,追悔莫及。记忆是读书的基本功,也是治学的前提,必须牢牢把握弱冠之年的黄金年龄,记忆、储存前人优秀成果。
其二,读书包括著书,要反复精读,“非颠倒数十百过不可”,需勤学、勤问、勤查书,不要苟且了事。更不要“读死书”“死读书”,读书要明辨是非,取是去非,吸收有益有用的东西。他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读书尤着不得一依傍之义”。所谓“不依傍”,就是要独立思考,自出新意,自成一家。世间事物在不断变化,所谓“新”“旧”,都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名为读书人,就应该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昨日新,前日陈;昨日陈,今日新;此时新,转眼陈。”“读书如观化,今昨无所住。”客观事物既然在不断变化,一个人的知识学问,也就应该与日俱进,随时俱变。在他批注的子书中,就表现出这种精神。
其三,读书与治学要专精与博综相结合。所谓专精,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专精下苦”,一是俗话说的“一通百通”。傅山先生在解释“专精”时说:“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打得破时,便处处皆融。”他在《家训》中教子孙如此熟读《左传》:“作一安身立命之所,作人、养性、学问,都向此中求之。”傅山虽然提倡专精,但并不满足于专研一书,而是通过一书打好学习基础,为进一步“博综”创造条件。他说自己“至三十四、五,始务博综”。其同学戴廷栻说他“二十以后,便读十三经、诸子”,以及宋以前的史书和佛经、道藏。他自己也说,“吾当二十上下时,读《文选》京、都诸赋”。可见从二十岁开始,他已博览群书,为后来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训子侄》中说:“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国语》《左传》《离骚》《庄子》《管子》,皆须细读。其余任其性之所喜者,略之而已。”把经、史、子、集的几部主要书籍,都加以细读,就是为了达到博而精的目的。
傅山先生的读书方法,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批注。读书时,把自己认为的重点和见解,用墨笔或朱笔,批在书眉、书缝之间,对于十三经、十七史,他都下过这样的功夫。
二是札记。边读书边作笔记,有的札记,还经过再一次的提炼和修饰,他的《荀子》《淮南子》手稿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是索引。编写索引,现在已经成为专门的学科,但在300多年前,傅山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先后编写完成《春秋人物韵》《地名韵》《两汉书姓名韵》。
四是删订。比如欧阳修的《五代史》,他认为有优点也有缺点,需“删削冗繁,而与其称谓不当者尽深涂易之以正名”。
傅山先生生前,除戴廷栻刊刻的《晋四人诗》中收录其少量诗、赋外,再无诗文著述刊刻,直到清乾隆十二年(1747)才由张耀先广泛搜罗刻成《霜红龛集》行世,并被后世不断将散落民间的诗文补入。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他自述的“著述无时亦无地”,更在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神。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批注的《荀子》《淮南子》读书札记为定本,但鉴于他学识渊博、眼光犀利以及读书方法的缜密,纵然自己不认为是精品,却已不愧于列入著作之林了。可以这样说,傅山先生读书也正是在著书,至少是在储备著书的材料。傅山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多体现在对于经史与诸子典籍的批注、札记、索引中,这也是他学术思想最重要的载体与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