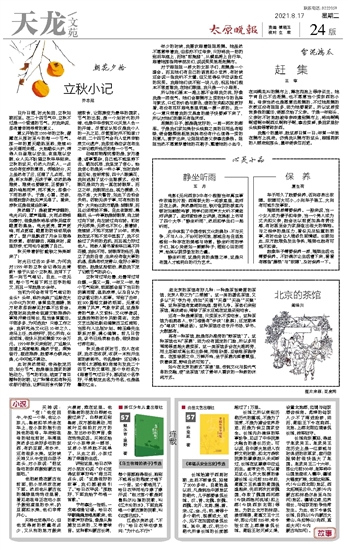年少的时候,我喜欢跟着姐姐赶集。她虽然不愿意带着我,但却拧不过母亲,只好将我一把扔到后车座上,而她“前掏腿”,从横梁跨上自行车,跟着她那些同学朋友们,说说笑笑地赶赴集市。
对于跟姐姐一样大的女孩子们,赶集是一个盛会。而且她们有自己的语言和小世界,有时候还会说一些我听不太懂、但又觉得似乎应该脸红的玩笑。我跟她们谈不到一块儿去,况且她们根本不屑搭理我,在她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小跟班。
所以她们基本一路上都不会跟我交流,好像我是一团空气。她们会聊集市上卖的纱巾的色泽与款式,口红的价格与颜色,谁的发夹配衣服更好看,有没有耳环跟电影里明星一模一样的。我一心一意只想着我的文具盒的盖子快要掉下来了,所以对她们的聊天有些厌烦。
赶集的日子,都是确定好的,一周一两次的频率。于是我们家如果针头线脑之类的日用品有短缺,便会翻箱倒柜地找找有没有什么值得一卖的玩意儿,搜罗出来,让姐姐或者父亲拿去换钱。姐姐当然不愿意穿着她的花裙子、戴着她的小丝巾,在鸡鸭乱叫的集市上,蹲在泥地上等待买主。她宁肯自己不去赶集,也不愿意当个卖东西的小贩。母亲当然也是愿意去赶集的,不过她赶集的次数还没有姐姐多,因为她要看家。所以这样卖货换钱的重任,便都交给了父亲。于是一年到头,父亲时不时地就被母亲派遣到集市上,将鸡啊鸭啊猪啊牛啊西瓜啊柿子啊,拿去卖掉,换回家里针头线脑等零碎东西。
我整个的童年,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集市上流走。仿佛我从集市的这头,跟随拥挤的人群走到那头,童年便倏忽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