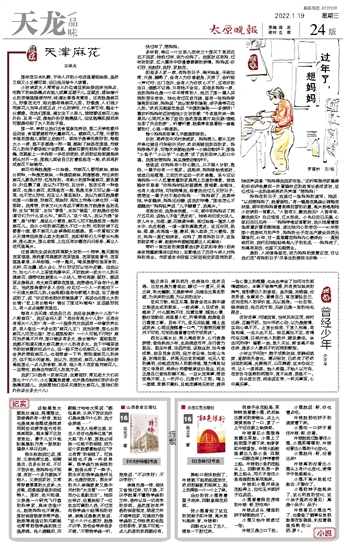多年前,单位一个女孩儿在年三十那天下班后迟迟不回家,她怕过年,因为没妈了。我那时还有妈,过年时的家,红火喜庆中弥漫着暖暖的亲情。妈妈说:你们好,我就好;我好,家就在。
和很多人家一样,有妈的日子,柴米油盐,平淡如常,只是,睡熟了,会有人为你掖被角;天凉了,会听到一声叮咛;出门在外,会有人为你放心不下;还有你的生日,谁都不记得,只有她不会忘。和很多妈妈一样,我的妈妈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经历了那一辈人共同的苦乐悲欣。她也有过花容月貌,留有一张妈妈穿旗袍的旧照,妈妈说:“我以前穿的旗袍,领子是带花边儿的。”然后无限留恋地说:“中国的旗袍——多美呀!”喜欢听妈妈年迈时唱她少女时的歌:“冬夜里吹来一阵春风/心底死水起了波动/虽然那温暖片刻无踪/谁能忘却了失去的梦”。听着听着,就像寒夜里看到一盏橙黄的灯,心里一阵滚热。
每个妈妈的故事几乎都是琐碎的。
幼时,寄养在中关村亲戚家。妈妈想儿,要从王府井单位骑自行车到中关村,然后再骑回东四的家。妈妈挣得不多,可每次来都给我带一小袋动物饼干,那些“小兔子”“小山羊”“小老虎”成了我的玩伴儿和口中福。我那时想妈妈,其实是想动物饼干。
爸爸说:你妈妈有个好心眼儿,从不跟人计较、抱怨,一辈子没有一个冤家。说起来,妈妈嫁给爸爸时,爸爸已经落难,之后历次运动一次次挨整。至今还记得妈妈一个人扛着笨重的家具爬上五楼的情景。爸爸晚年叹息道:“你妈妈年轻时挺漂亮,爱唱歌、会唱戏,也有人追求她,可她同情我,跟着我没过几天好日子,想想这一辈子对不起你妈妈……”妈妈病了,我陪伴她,半夜醒来,妈妈还没睡,说我打呼噜,“那您怎么不推醒我?”妈妈轻声说:“儿子睡着了,我高兴。”
有段时间,我身体消瘦。一天,病中的妈妈买了两斤五花肉,说给儿子做“虎皮肉”。她将肉切成大块儿,放入冷水,加葱、姜、花椒煮半熟,再过油煸一遍放入凉水中,肉皮起褶,一道一道的真像虎皮。这还没完,热油,葱、姜、肉再煸一遍,最后,倒入老汤,文火慢炖。那天,妈妈一直忙到深夜。没妈了,想有妈的日子,这些琐碎家常小事,桩桩件件都能咂摸出人间真味!
常听一首古老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后来李叔同重新填词《送别》),这歌唱出了古往今来人对妈妈的思念。作家凌叔华弥留之际回到史家胡同的家,她低声说道:“妈妈等我回家吃饭。”还听军旅作家蔺柳杞伯伯讲他最后一次看望年迈的老首长杨成武时,这位戎马一生的战将突然失声道:“想妈妈!”
妈妈在的日子,我画过一些妈妈的速写。她说:“以后想妈妈了,就看画吧。”有一幅是在奥森公园银杏林里,病中的妈妈看着周围玩耍的幼童,高兴地唱起她小时候的一首歌儿:“人皆有父,翳我独无?人皆有母,翳我独无?白云悠悠,江水东流。小鸟归去已无巢,心欲归去已无舟……”妈妈哼唱这首歌时,我从她看着那些顽童欢喜的眼神里,读出她内心的悲伤——41年前那个浩劫年月的严冬,妈妈的长子在生产建设兵团无辜惨死;41年,它一直埋藏在妈妈内心最深处……直到临终时,我听见她轻轻唤起儿子的乳名……妈妈走了,别离有哀伤,也留下无限想念。
是的,人间值得留恋,因为妈妈的爱意还在,它让我们在“有妈的日子”尽享生的美丽与欢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