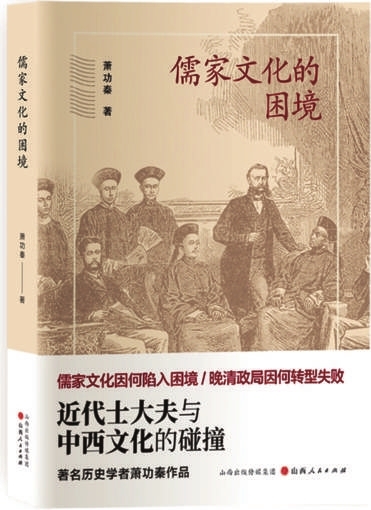不妨从“三跪九叩”谈起。
乾隆时期,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携带600箱贺礼漂洋过海来中国,请求扩大通商之时,却让清王朝的士大夫们犯了难,难的不是是否通商,而是是否下跪。在觐见皇帝的“三跪九叩”礼上,特使说了“不”,理由是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或属国,为何下跪?几番“开导”未果,马戛尔尼提出,要由一名与他官阶相当的中国朝臣身着朝服在英国君肖像前行三跪九叩礼,他本人才会向乾隆帝行同样的跪拜礼。这在士大夫们眼中就是冥顽不灵:一个使臣胆敢挑战天朝法度!马戛尔尼碰了一鼻子灰,所有要求被严词拒绝且被勒令早日出境。
这一幕啼笑皆非,然而从认知心理角度看,不足为奇,因为人们往往运用既有认知及认知范围内的思维模式认识外部世界,而在士大夫们构建的儒家思想宫殿内,能找到的不外“华夏中心”“内夏外夷”“用夏变夷”云云。
20多年后,英国再次派特使阿美士德前往嘉庆朝,士大夫们为了避免“没有教养”的特使故伎重演不尽礼数,一方面安排专人教其叩跪之礼,另一方面由尚书和世泰领衔上演“疲劳战”,期待疲惫不堪的使团无力招架任凭摆布,从而糊里糊涂完成三跪九叩。然而面对坐等许久的嘉庆帝,阿美士德抛出拒绝理由:觐见文书、礼服均在落后的辎重车,而自己不能穿着脏污的便服觐见皇帝。朝堂悻悻,办事不力的导演和世泰只好谎称使臣生病不愿入朝,不了了之,阿美士德被驱逐出境。
两次不欢而散的交锋后,同治帝亲政大礼前夕,俄英法美等驻华公使要求依国际惯例参加觐见,并提出按《天津条约》相关条款行免冠鞠躬礼。这让已见识过西方侵略者实力的士大夫们内心备受煎熬,毕竟形势不同往日。此时,御史吴可读的一封奏折,奇迹般化解了满朝尴尬。奏折称“洋人无异同于禽兽,使其行三跪九叩之礼,有如强禽兽而行五伦之礼,能使其行,不为朝廷之荣,不能使其行,亦不足为朝廷之辱。各大臣以为不能使各国使臣从中国之礼,为中国之羞,臣窃以为,使各国使臣行中国之礼,反为中国之羞”。此番言论,不过是苦闷的士大夫摆脱屈辱感的心理自卫。如此,既可堂而皇之地接受屈辱的事实,又能使内心免遭这一事实带来的屈辱感。
随着中西冲突激化,西方侵略加剧,国人的仇恨与屈辱日渐积累。此时,迁怒不失为一种良策。遍观周遭,与洋人相关、不会引发洋人反攻击、具有“不合儒家圣教”正当攻击理由的西学,自然成为精英人士纾解仇恨、发泄情绪、平衡心理的目标。正统士大夫们也会将迁怒对象辐射至郭嵩焘、曾纪泽等西学的拥趸者,从而以更顽强的姿态反对西学中用。
白银外流,土地瓜分,百姓流离,西方势力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让侵略合法化,百姓们一次次忍无可忍的反抗换来了更残酷的镇压。佯装视而不见或无关痛痒地迁怒,已无法扑灭目睹国之不国的士大夫们内心的焦灼,正当他们积累的怨愤、屈辱无处安放时,义和团出现了。洋人欺凌引发的屈辱重压让人窒息,他们多想在正面战场痛击强大的敌人,抑或在谈判桌上挽回丧失的尊严,然而手中的兵器终究敌不过洋枪洋炮,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也早已让敌人占尽先机,怒火中烧却宣泄无门的他们早已顾不得其他。
《儒家文化的困境》是萧功秦先生的代表作。近代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扰、战争,先后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总体来说,咸丰之后,士大夫才逐步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并在不断认知西方世界的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由此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但其中也充满了矛盾,所以也就有了天津教案和庚子国变,而这恰恰是士大夫儒家文化的固有心态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不可避免的挫折。萧功秦先生深刻探究了这一过程,本书所揭示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值得后世子孙警醒、警惕。